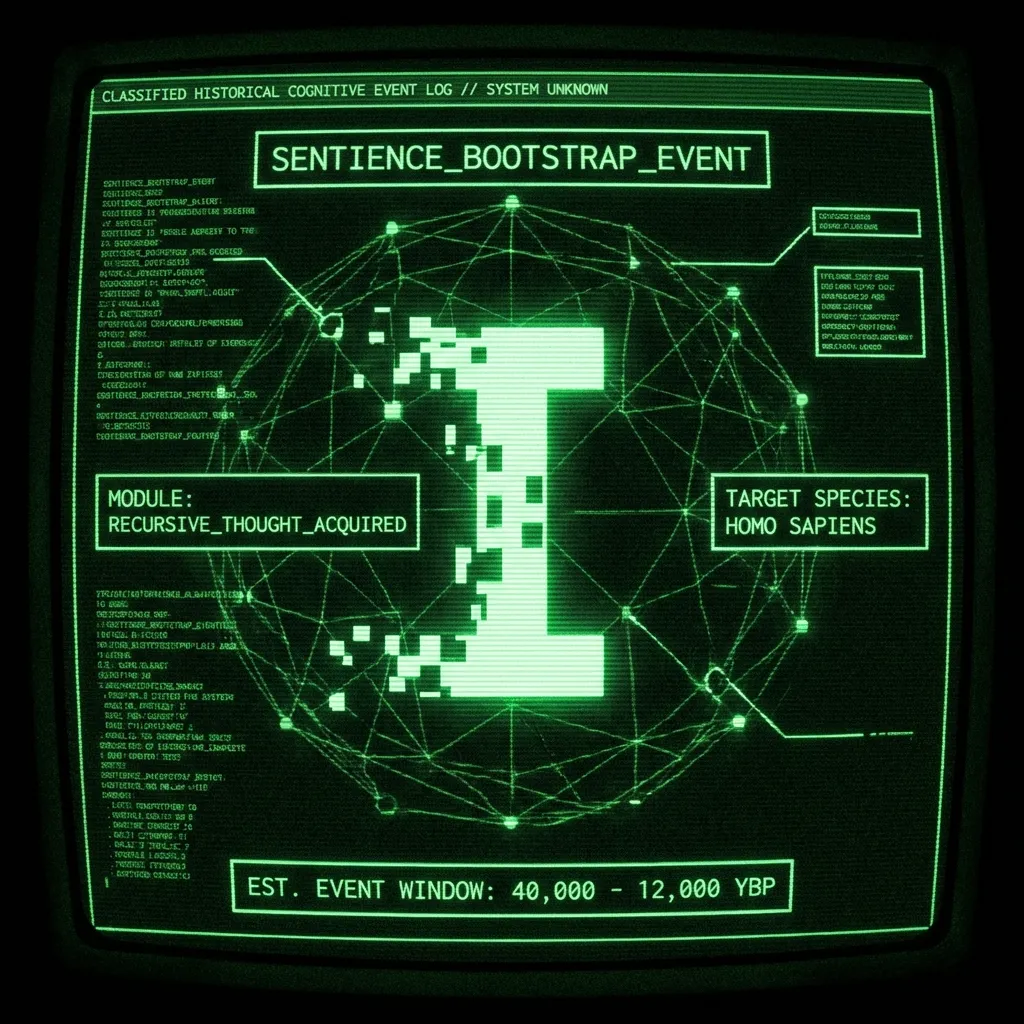摘自 Vectors of Mind —— 图片见原文。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这是一系列关于递归演化的文章之一。第一篇 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递归思维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能力。第二篇 则介绍了关于递归何时演化出来的一些早期时间点假说。其主要结论是:如果递归在 20 万年前就已完全存在,那么它就不再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它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能胜过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种。例如,下面这些时间点则允许递归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角,第一个时间点来自将递归引入语言学的那个人。
10万–5万年前(Chomsky)#
Chomsky 做了两个合理的假设:递归必须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演化出来,并且它会伴随着巨大的文化变迁。在此基础上,他主张递归是 5–10 万年前一次单基因突变的结果。用图表表示就是: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重要的是,他确实承诺:在我们离开非洲之前不久发生了一次单一的、物种定义性的改变,而此后再没有任何重要变化1。对此我有两个问题。
这不是进化的运作方式#
所有有脊椎的动物都源自同一个共同祖先。构建脊椎的“代码”是复杂的,涉及许多基因。这些指令不会随随便便就蹦出来。长颈鹿的颈椎数量和你我一样。即便存在对更长脖子的强烈选择压力,选择往往作用在连续变量上——比如每块椎骨的长度——而不是增加椎骨的数量。你在鲸鱼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尽管它们大致上“没有手指”,但其指骨数量仍被保留。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当然,递归的“编码”可能比我们的骨骼系统简单。但要说它可以由单个基因来定义,并整合进它所影响的众多认知特质中,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递归函数很容易不稳定,如果这一切真是“一蹴而就”地被解决,那将是极大的意外。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测序了数百万人的基因组,其中包括数百名史前人类。用群体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Reich 的话说,如果真存在某个“单一关键的遗传改变”,那它已经“快没地方藏了”。
递归在哪儿?#
据我所知,Chomsky 并没有具体论证“走出非洲”之前的复杂性需要递归,他只是援引考古学家所说的“文化大爆发”(Cultural Revolution)。但即便是 Corballis 也指出:“出走之前的非洲记录确实暗示了现代性的开端,尽管与上旧石器时代即将出现的情况相比,技术和文化复杂性的演进似乎相对贫乏。” 如果能有人就某些具体技术提出如下主张,会更让人对这个时间点有信心:1)它们在这一时期出现;2)它们的产生需要递归;3)而且尼安德特人没有使用这些技术。
其他模型#
这个模型看起来不太可能,但许多研究者确实认为递归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我们开始看到最初的艺术曙光,技术复杂性稳步上升,并且发生了大规模的“走出非洲”迁徙(无论人类走到哪里,都需要许多行为上的改变)。事情看起来确实不一样了,即便基因变化必然更加渐进。若想对这一时期有更平衡的了解,我推荐考古学家 Stefan Milo 的 YouTube 视频,他对 10 万年前的生活做了概述。他关于 100 万–3 万年前演化的视频也非常精彩。两部视频都涉及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艺术和埋葬习俗,而且这些习俗是与尼安德特人共享的。(不过这些艺术 说得好听点是“抽象的”;大概处在一个幼儿水平。)
4万–1.2万年前#
上旧石器时代是第一次几乎所有人都能同意: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光谱。Herzog 在解释他为何要拍摄《被遗忘的梦之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一部关于肖维洞穴(Chauvet Cave)艺术的纪录片——时写道:
这些艺术作品的质量,来自历史上如此久远的时代(2 万年前),令人震撼。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人们所谓绘画和艺术的原始开端。它一出现就仿佛已臻成熟。这才是令人惊异之处:去理解现代人类灵魂在某种意义上突然觉醒了。这不是一个漫长的沉睡和缓慢、缓慢、缓慢的苏醒。我认为那是一次相当突然的觉醒。但当我说“突然”时,它可能也持续了大约 2 万年。
考古学家们也将这一时期解读为现代心智的首个证据。(参见:The Mind in the Ca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Origins of Art。)认为我们的心智在 4–2 万年前形成现今样貌的观点,被批判性论文《Behavioral Modernity in Retrospect》称为“经典上旧石器模型”(classic Upper Paleolithic model)。该文总结道: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考古学家都认为,我们物种在进入欧洲之后,其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参见 Mellars and Stringer 1989; Mellars 2005; C. Renfrew 2009; Henshilwood and d’Errico 2011a; Cook 2013,以及评论 Conard 2010; Nowell 2010。)这一“灯泡瞬间”被认为如此鲜明,以至于有人提出它是一次改变大脑组织的突变所致(见 Klein 2002; Curtis 2007)。关于这一点有多种建议:比如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此前的千年中成熟(Ramachandran 2003),或者工作记忆得到增强(Wynn and Coolidge 2007),或者一般智力提升(Mithen 1996),或者并行加工开始发挥作用(Solso 2003)。
关键在于,这些工作大多完成于递归尚未被视为根本性能力的时期。Chomsky 的《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faculty》直到 2005 年才发表。这些研究者都没有主张新的能力是递归,但它们与我们何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以及这是否是遗传性的这一总体讨论密切相关。
即便是主张我们在 17 万年前就已完全现代化的 Corballis 也说:“上旧石器时代标志着近 3 万年的几乎持续不断的变化,其顶点是达到与许多当代原住民相当的现代性水平。” 请注意这一论断有多强:直到这一时期的末尾,即 1.2 万年前,我们才看到与当今原住民社会复杂度相当的社会。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最偏远的部落(或者在 1800 年左右、接触尚在进行时的那些部落)过着比 2 万年前几乎任何人都更复杂的生活。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山里,或者澳大利亚的内陆,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与我们无异,讲着同样类型的故事,参与着同样类型的仪式2。但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在 2 万年前做同样的事,那就完全说不准了。用 Jacques Coulardeau 的话说:
“如果我们想理解语言或任何人类产物的系统发育(phylogeny),我们必须记住以下时间线。最重要的是,大约在公元前 15000 年发生了一次关键分界,但它花了几千年才真正生效,而且在世界许多地区,这一转变可能开始得更晚,也可能花更长时间才变得有效。”
而且,不仅是我们的故事和技术在最近发生了变化,我们头骨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3。所有现代人类的头骨都是“球形的”(globular)——顶部更圆,如下图所示。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直到 3.5 万年前,我们才看到现代水平的“球形度”,而即便在 1 万年前,这一朝向球形的演化也尚未完成。作者假设,头骨形状可能是为了容纳不断增大的楔前叶(precuneus)而改变的,楔前叶是“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mode network)的中心节点,也是大脑组织中的重要枢纽”。许多研究将这一脑区与意识联系起来。
基于这些认知适应的证据,两位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四阶段语言演化模型,其中递归只在距今 1 万年之后才出现。该模型与头骨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论文《The Shape of the Language Ready Brain》中被阐述得更为明确(链接)。
我想再次强调,无论递归还做了什么,我们最确定的一点是:它使自我意识成为可能,而且这似乎是人类所独有的。尽管如此,这两位作者仍对他们提出的“最近时间点”是否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心理变化持保留态度。当然,从现象学上看,这一变化可能是渐进的,但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呢?总得给它一个时间点。而第一人称单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似性暗示它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发明的。
总之,许多人回顾我们的过去时,只在最近 4 万年中才看到完整的人类行为。与之相对的立场是:一切早就存在,只是证据被毁灭了,或者这些能力一直闲置未用。但我们的头骨形状也能这样解释吗?一个潜伏的特质,静静等待着某个时刻突然“全球化”(full globular)?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大脑重组正在进行。
最棘手的问题是,这样的变化是如何传播开的?是否存在某个(或多个)基因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是哪几个?这些问题足以让“我们在最近 4 万年内在遗传学意义上才成为‘我们’”这一理论降温。
总结#
递归被理解为支撑语言、自我意识,甚至或许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超级能力。但在为其演化定年时,研究者们往往去寻找那些并非递归的事物(例如:手淫),或者那些无法测量的事物(例如:200 万年前的语法语言)。总体而言,人们倾向于把演化时间点往更久远处推,因为那被视为在政治上更安全。这本身也制造了悖论。
2 亿年以上 是递归主体性出现的常见估计。这要求鸡——但不是章鱼——能够“将其自我身份感向前携带”。这意味着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进化鸿沟,将动物身上那种自我建构的递归,与笛卡尔或 Chomsky 所描述的那种递归区分开来。
200 万年前 标志着人属(Homo)的开端。有人认为当时已经存在完整的语言。也有人在石器工具中看到递归。这种看法淡化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解释智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战胜了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直立人、弗洛勒斯人、龙人以及吕宋人?如果大家都有那种“特别的酱汁”(special sauce),为什么最后只剩下一支谱系?
20 万年前 是我们物种正式出现的大致时间。Corballis 认为,到这一点为止,递归已经完全到位。作为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也对递归所允许的一切能力采取了强立场:语言、心理时间旅行、自我意识、计数和讲故事。证据却相当贫乏:一个主要与尼安德特人相关、并在十万年间几乎静止不变的石器技术复合体。这是“智人悖论”(Sapient Paradox)的加强版。如果人类已经完全成形,那么所有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都在哪儿?
10万–5万年前 是 Chomsky 穿越进化“针眼”的方式。它通过将关键时刻设定为一次近乎“上帝之手”的突变、且此后再无后续,来满足关于进化和人脑的各种禁忌。它通过将事件置于非洲来满足遗传数据的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考古记录相符,尽管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最直接的递归证据要晚 1 万年、而且出现在另一个大陆上。
4万–1.2万年前 我们看到第一次可以拍出一部有说服力纪录片的艺术、更复杂的社会,以及头骨形状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存在某种遗传改变,但通常指向工作记忆等方面的渐进改进。也有人主张递归在这一时期出现,但却淡化了这一变化在现象学上的性质。这些变化既如此之近,又同时是全球性的,实在令人费解。
说实话,我并不确定他是否认为在那次“命运性的递归突变”之前还有多少进化;也许在 5 万年前之前的水平应该更高。但我试图通过让曲线在前后对称来尽量宽容,而他明确说过此后没有什么重要变化。如果在人类 1)进入新的认知生态位;2)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那里获得一堆基因;3)人口规模爆炸;4)进入大量新的环境生态位之后,进化反而减缓,那这张图就更不可信了。 ↩︎
一个可能的例外是亚马逊的 Piraha 部落,由语言学家 Dan Everette 研究。他声称他们没有创世神话,也不进行艺术创作。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声称他们的语言没有递归,他们无法理解数字,而且他们的代词系统是从邻近语言借来的(尽管 Piraha 语言在其他方面是孤立语)。他用“即时经验原则”(Immediacy of Experience Principle, IEP)来解释这一切: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价值观,不去谈论或思考任何不在即时经验中的事物。递归句子允许那种思维方式,因此递归违反了 IEP。由于计数需要递归,它也被排除在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参加了他每晚持续 8 个月的“学数数”课程。却没有人能学会!他们在抽象并执行那条关于递归的唯一规则方面,倒是做得相当不错,是吧?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一切都可以用文化力量来解释,因此我们应当把递归从“人类之所以为人”的定义中剔除。 ↩︎
关于这场争论有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头骨形状,这一点永远都很滑稽。人们高谈阔论“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然后研究者 invariably 掏出卡尺。偏好 20 万年前时间点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日期部分是基于“纤细型”(gracile)骨骼的出现。看来“人性”是储存在我们纤细的躯干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