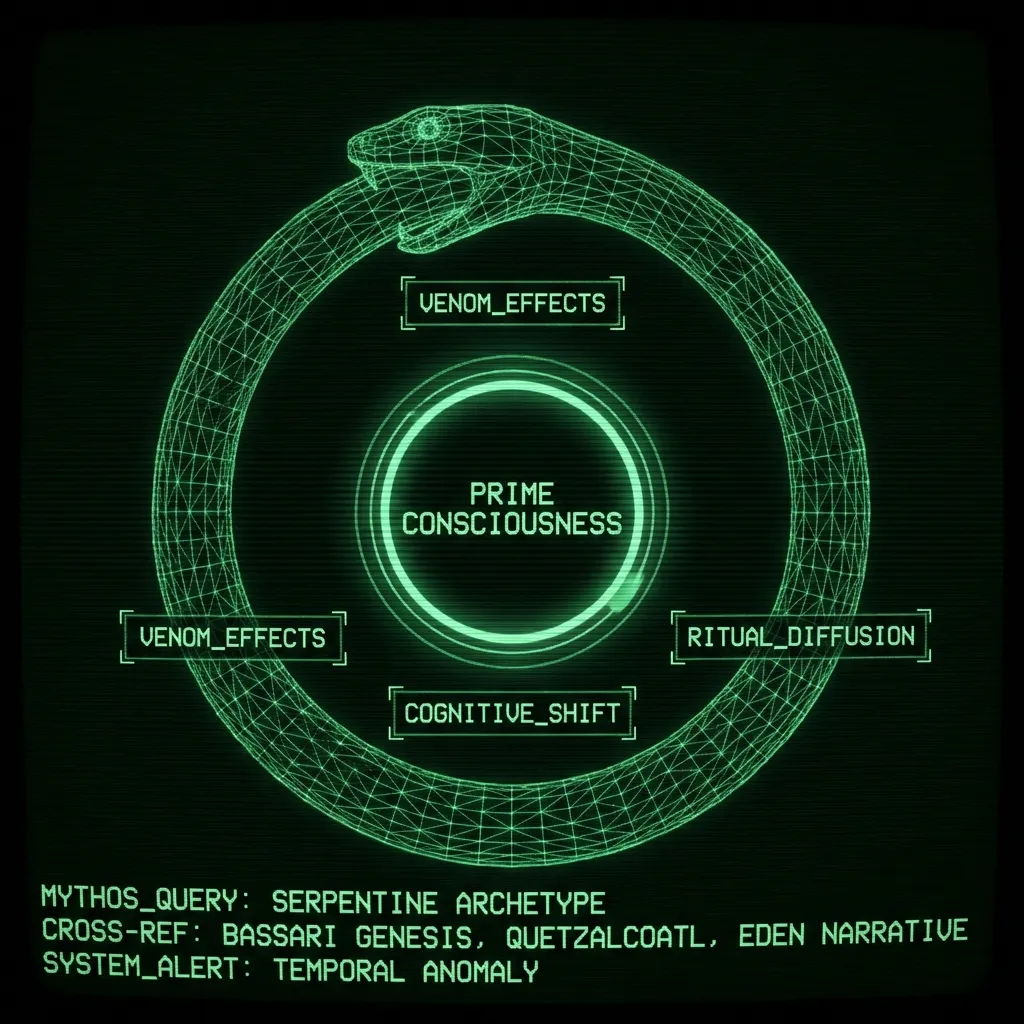摘自 Vectors of Mind —— 图片见原文。
[图片:原文中的视觉内容]羽蛇神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黎明之主,与金星有着密切关联,与路西法类似。在这幅描绘中,眼睛从他头上伸出的蛇身上长出。
太初之时,上帝创造了三种存在:人、羚羊与蛇。那时只有一棵树,结着红色的果实。每隔七天,上帝便会从天而降,采摘果实。某日,蛇提议他们也该吃这果子。起初,人和他的妻子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吃了果子。下次上帝降临时,他质问是谁吃了果子。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并将责任推给蛇。作为惩罚,上帝给了蛇一种药,使其可以咬人;同时赐予人类农业和不同的语言。
两年前,我提出一个观点:通过迷幻仪式,“自我”这一概念被发现并以模因的方式扩散。这导致了人类心理的根本性改变,并被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中。须知,上面的创世神话并非出自《创世纪》——尽管你完全可以原谅自己会这么以为。这个故事是由西非巴萨里人(Bassari)讲述的,1921年由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记录。他特别强调,当地尚未受到传教士影响;这个故事在巴萨里人中广为流传,被视为其古老遗产的一部分。
其与《创世纪》的相似之处极为惊人:最初的一对男女、七天、蛇的诱惑、禁果、神罚以及农业。如此相似的故事如何能在相隔大陆的地方独立出现?哈佛语文学家迈克尔·维策尔(Michael Witzel)在《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Mythology》中提出,包括巴萨里的蛇、路西法与奎兹尔科亚特尔在内的创世神话相似性,源自一个共同的神话根源,该根源早于人类走出非洲,最终可追溯至十万年以上。但这带来的谜团多于解答。如此具体的细节如何能在十万年的口耳相传中存续?如果创世神话如此古老,为何直到五万年前我们才看到任何叙事性艺术?没有证据表明十万年前已经存在创作神话所需的抽象思维。事实上,“智性悖论”(Sapient Paradox)正是困惑于:诸如艺术之类的“智性行为”,为何直到约一万年前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出现。
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文化扩散。最新的基因证据显示,农业、陶器和新工具是由来自欧洲和黎凡特的移民在大约七千年前开始引入北非的1。或许这些新来者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宗教与创世神话。
巴萨里的创世故事只是更广泛模式的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到中国再到澳大利亚,蛇在创世神话中无处不在。要体会这有多反常,不妨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蘑菇都被视为人类处境的始祖。羽毛真菌奎兹尔科亚特尔为最初的一对男女注入灵魂。因陀罗用香菇之杖搅动乳海,获得不死甘露。菌丝之母向夏娃献上知识之果。在每一块大陆上,岩画都呈现出类似的变体:
[图片:原文中的视觉内容]生命之树,由 MidJourney 生成
在这样的世界里,自然的结论会是:蘑菇在人的文化演化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如果这种实践足够久远,甚至可能影响了认知演化。在《蛇之意识教派》(The Snake Cult of Consciousness)中,我论证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只不过原初的致幻剂不是蘑菇,而是蛇。蛇毒是一种药物,被用于仪式,而各文化中最古老的故事都将蛇与意识联系在一起。在冰河时代末期,这些蛇毒仪式帮助催化并传播了人类的自我意识。因此,伊甸园中才会有那条蛇,献上“知识之果”。
问题在于,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不是吗?蛇毒真的能让人“嗨”吗?创世神话究竟能存续多久?如果它们是对人类处境被发现这一事件的记忆,那么人类认知硬件究竟是多近才演化出来的?是否有任何专家相信哪怕与此略为相似的观点?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蛇教”假说表现得出乎意料地经得起推敲。接下来是对支持这一假说的惊人证据的回顾,包括:
一个主流版本的“蛇教”理论
蛇毒是一种“神圣致幻剂”(entheogen)
近期认知演化的遗传学证据
旧石器时代神秘教派在全球传播的考古证据
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阅读原始长文。不过,下一节会先概述基本论点。
换个名字的“蛇教”#
在 2015 年的《Rock Art Research》中,认知神经科学家汤姆·弗罗泽(Tom Froese)提出了论文《The ritualised mind alteration hypothesis 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symbolic human mind》(“仪式化心智改变假说:象征性人类心智的起源与演化”)。他将旧石器晚期岩画解读为一种萨满教形式的开端,用以教授“主客体分离”:
“这里我们回到先前已经讨论过的一个主题,即迷幻物质的摄入会深刻打断正常的心理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实现这种打断的唯一方式,但它们无疑是一种强有力且对大多数文化而言易于获得的选项。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反思性意识对年幼婴儿的必要性较低,但随着成长,它变得愈发有用,并且至少在高度象征性的文化语境中,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一视角看,传统上在青春期进行的强烈成年礼——包括禁忌、长时间的隐居、社会隔离、身体苦难以及迷幻物质的摄入——即这些与性成熟过程本身几乎无关的实践(van Gennep 1908/1960),就不再像看上去那样怪异了。这些仪式的最初目的,可能与促进年轻入门者那种通常完全情境化的心智,向一种更稳定的主客体二元形式的个体发生发展有关,而这种形式更适合被纳入象征性文化之中(Froese 2013)。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通过社会强化来促进心智发展的最初目的会变得不再那么关键,因为我们与我们的文化环境共同演化,使得个体更容易适应并再生产多种高度象征性的实践(Froese and Leavens 2014)。这一共同演化过程在人类大脑与语言的共同演化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Deacon 1997)。相应地,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不应期待所有传统文化仍然使用深度心智改变的方式,因为一旦我们对高度精细模仿象征性实践的倾向与能力已经到位,现有的象征内容便可以在没有这些方式的情况下被保存与发展。”
古老的入门仪式常常将入门者带到死亡边缘,在那里他们会发现,当身体开始衰败时,究竟有什么仍然存在。在这种“门槛状态”中,有某种东西得以延续:一种我们如今称为“我”的意识残余。这些对死亡的受控触碰揭示了意识与肉体的分离——不是通过论证,而是通过直接经验。这种对“我”独立于身体存在的具身展示,是发展稳定元认知的关键。这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法:不讲道理,而是“示之以行”,并将其推向逻辑极致。如今这已不再必要,因为象征性思维在数千年前就已成为参与文化生活的基本门槛,因此人类已经演化为无需针对性的仪式干预也能发展出主客体二元性。弗罗泽的假说大致如此。
弗罗泽博士如今是《Adaptive Behavior》的主编,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一模型是可行的,并解决了许多与人类演化相关的问题。岩画可以追溯到约五万年前,因此这些实践必然是在此之后某个时间被发明,在随后的数千年中构成重要的演化压力,而如今只在残存的仪式中被隐约记忆。在当下,“死亡与重生”大多只是象征性的,比如基督教的圣餐礼2。耶稣替你而死,所以你无需再死。但在最初,你才是那位祭品,而在死亡中你会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与我提出的“蛇教”理论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我更强调这些实践的扩散过程。你可以在这期播客中听到我们讨论他的理论,在那里我有机会提出蛇毒作为原初“神圣致幻剂”的可能性。他立刻意识到,这解决了“发现难题”——蛇会自己来找你!在很早期,可能已经存在一些旨在产生改变意识状态的仪式,比如禁食与隔离。某个人被蛇咬后意识到,在与毒液搏斗的过程中,他获得了同样的状态,这就可以与解毒剂一起被纳入仪式体系。
如果有人在计分,这一发展将“蛇教”从“连边缘都算不上的理论”推进到了“稳稳的边缘理论”。算是进步!其他与之互动的科学家包括具有遗传学与神经科学背景的 Nick Jikomes(其平台为 Mind & Matter),以及由一位生物学博士运营的在线期刊 Seeds of Science。在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最令我惊讶的一点,是这一领域仍然存在极大的开放性。我们根本没有一个良好的模型来解释我们的独特智能究竟何时、如何演化出来。而且,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即便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也表示,我们需要纳入“近期演化”的全新模型。
蛇毒 RAVE 派对#
除了说“蛇教”理论更像数字命理学而非科学之外,最常见的批评是:蛇毒不是药物。那么,我很抱歉,可他们为什么会在狂欢派对上贩卖它呢?
[图片:原文中的视觉内容]2024 年 3 月 18 日,《The Tribune of India》报道
Yadav 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知名 YouTuber,而他的被捕发生在我写完“蛇教”那篇文章之后。在原文中,我只能引用一些学术文章,比如《Snake venom – An unconventional recreational substance for psychonauts in India》(“蛇毒——印度心灵探险者的一种非常规娱乐性物质”),其中提到,耍蛇人会在全国各地经营“蛇窝”(对思考者而言的“鸦片馆”)。这对我的批评者来说还不够,其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读文献。因此,Yadav 的蛇毒案在挖掘视听资料、澄清“蛇之状况”方面可谓大有裨益。在邻国巴基斯坦,Vice 访问了一家蛇与蝎毒成瘾康复中心。在 Psychiatry Simplified 频道上,Sanil Rege 医生找到了展示致醉方法的影像资料:
“牙咬舌头”显然是“吞云吐雾魔龙”的常见方式,我们稍后还会回到这一点。现在,你也许会抗议说,蛇毒不过是派对用药,这并不能证明它曾被用于仪式。在这方面,印度最受欢迎的古鲁之一 Sadhguru 在一段标题颇为贴切的 YouTube 视频《The Unknown Secret of how Venom works on your body [practical experience]》中给出了答案3:
“毒液对一个人的感知有显著影响……它会在你与身体之间带来一种分离……它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会让你永远分离……我在许多不同场合摄入过毒液……有一次我因蛇咬而死去,另一次我又因蛇咬而复活。”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解离剂,而这正是医生为催化元认知所开的“药方”4。回到西方科学的世界,蛇毒也正被积极研究用于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因为它能够靶向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s)。这篇 2018 年的论文甚至声称:“因此,蛇毒 AChE 是设计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的最佳来源。”这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并非没有先例:现代的“万能药”——毒蜥毒素(Gila Monster venom)制成的药物(Ozempric),以及古典的“万能药”——蝮蛇肉制成的解毒剂(Theriac)。
任何对“嗑药猿理论”(Stoned Ape Theory)抱有同情的人,都应该更偏好“蛇教”理论,因为蛇毒完全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此外,蛇在创世神话中无处不在,而蘑菇则几乎完全缺席。我的意思是,这就写在《圣经》里。带来光明的,是一条蛇!5
人类大脑何时演化完成?#
如果创世神话是对早期演化状态的回忆,那么在神话可存续的时间长度上,必然存在极其强烈的选择压力。那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有非常强的证据表明,神话可以存续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因为有许多关于冰河期末海平面上升的传说案例。比较神话学家还认为,以蛇为主角的全球神话模式、原初母系社会、创世叙事以及昴宿星团等,表明这些神话可能已存续数万年。尽管这一点颇具争议,我们姑且保守地采用一万五千年的上限。在这段时间里是否发生了显著的演化?按照标准模型的说法:没有。
上图展示了我们何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由进化生物学家尼古拉斯·朗里奇(Nicholas Longrich)绘制。“现代 DNA”被标注为在 26 万至 35 万年前已经确立,那时科伊桑人(Khoi San)被估计从人类家谱的其余部分分支出去。语言、艺术、音乐、灵性、舞蹈、讲故事、婚姻、战争与双亲抚育如今定义了我们的物种,因此人们假定这些在当时也是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直到约 6.5 万年前开始的“伟大飞跃”才有证据显示这些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智性悖论”正是困惑于:艺术、宗教与抽象思维为何直到约一万年前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出现(“蛇教”那篇文章试图对此给出解释)。
这一模型假定,在过去 30 万年间,认知能力并未发生演化。近期的遗传学研究表明,这一假定是错误的。今年,一家顶尖古代基因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在过去一万年中,“定向选择”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收集了数千份古代 DNA 样本,发现较早期的样本往往携带与某些特质相关的基因,比如行走速度、吸烟与智力。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万年中,我们一直在朝着“更聪明”的方向演化。请看补充材料中的这张图,它展示了按死亡时间推算的平均智力(由基因推断):
基因数据表明,约九千年前的古人类平均携带的基因变体,对应的 IQ 分数比当今人群低 2.3 个标准差(约 34.5 分)。这意味着当时的平均遗传 IQ 潜力大约为 65.5。如果我们将这一变化率线性外推回三十万年前,就会得到毫无意义的负数——低于 -1000 的 IQ 分数。即便采用更保守的线性估计,即每一万年变化 0.79 个标准差(红线),三十万年前的 IQ 仍会是不可能的 -255.5。虽然这些外推显然是荒谬的,但它们凸显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如今已经有了“硬证据”,表明在短短一万年中发生了显著的认知演化。这暗示五万或十万年前的人类,可能在认知上与我们有着远比此前假定更大的差异。
这与考古学证据相吻合。十万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元认知的证据,而如今元认知却是人类的普遍特征。科学的一大谜团在于:如果基因分支早在三十万年前就已发生,这种变化如何可能?“基因—文化共演”给出了答案。如果存在某种方式可以教授元认知(或语法语言,或“我是”,或无论《人类简史》中所谓的“智人特制酱汁”究竟是什么),那么这种能力就可以跨越基因谱系传播。“蛇教”理论提出,最强的演化压力在于发展出一个无缝的“自我建构”,并且要在幼年时期就完成这一过程。
产出上述基因数据的实验室负责人大卫·赖希(David Reich)将古基因组学比作伽利略的望远镜,即将颠覆我们当前的人类起源模型。正如望远镜揭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一样,基因证据正在显示,人类演化并未在三十万年前“方便地”停止。正如赖希所言,我们正处在理解人类演化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门槛上。“仪式化心智假说”——即意识本身是通过文化实践演化出来的——为“我们如何成为人类”这一长期谜题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答。
这项基因研究还揭示了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模式:近期演化同时影响了精神分裂症与吸烟行为。这一关联并非偶然——70–80%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吸烟,很可能是因为这两种状况都涉及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s)。这些神经受体对认知与意识觉知至关重要。如果你还记得前文所述,蛇毒之所以被研究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6,正是因为它靶向 nAChRs。
我并不是在暗示,蛇毒仪式是驱动针对精神分裂症与吸烟行为选择压力的主要因素。相反,在过去五万年中,象征性思维逐渐成为参与社会生活的“入场券”。起初是断断续续的爆发,随后则是一哄而上。早期有成千上万的部落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对内在生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且往往脆弱)。某个群体发现,蛇毒可以可靠地诱发“你与身体之间的分离”。这一实践连同相关的神秘教派与文化创新一起传播开来,因为它“有效”,或许发生在冰河时代末期。蛇毒靶向的神经受体,恰好也是近期演化所作用的对象,这一事实构成了颇具吸引力的支持性证据。
这一假说给出了可检验的预测:我们应该能在旧石器晚期发现改变意识的仪式传播的证据,而这些实践应当充斥着蛇的象征。被研究了一个多世纪的“呼啸板”(bullroarer)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想想“呼啸板”吧#
[图片:原文中的视觉内容]一件距今 14,000 年的法国呼啸板
呼啸板是一个简单的物件:一块木片、骨片或石片系在绳子上,甩动时会发出嗡嗡声。这种东西完全可能被多次独立发明。然而,围绕它的仪式性联想在全球范围内却惊人地相似。早在 1920 年,人类学家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就写道:
“问题不在于呼啸板究竟是被发明了一次还是十几次,也不在于这种简单玩具究竟是一次还是多次被纳入仪式关联。我本人曾亲眼见到霍皮族(Hopi)长笛兄弟会的祭司在极为庄严的场合甩动呼啸板,但我从未想到要将其与澳大利亚或非洲的神秘仪式联系起来,因为那里并没有任何暗示表明,女性必须被排除在这一器物的影响范围之外。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为什么巴西人和中澳大利亚人会认为,女性看到呼啸板就得处死?**为什么在西非、东非与大洋洲,人们如此一丝不苟地坚持要让女性对这一事物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有什么心理学原理会驱使埃科伊人(Ekoi)与博罗罗人(Bororo)自发地禁止女性了解呼啸板,在这样的原理被提出之前,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从一个共同中心扩散的假设更为可信。**这将意味着,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与非洲的男性部落社团入会仪式之间存在历史联系,**并将进一步强化这样的结论:性别二分并非一种自发源于人性需求的普遍现象,而是一种起源于单一中心、随后被传播到其他地区的民族志特征。”
洛维在现代人类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两度担任《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主编。他绝非边缘人物。1929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 E.M. Loeb 在此基础上补充道:
“关于扩散的论证甚至比Lowie所说的更有力。牛吼器不仅在与男性启蒙仪式相关时对女性是禁忌的,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表现为灵的声音。牛吼器在与男性启蒙仪式相关时也从不单独出现。本文已经证明,在男性部落启蒙仪式中,一种形式的部落标记、死亡与复活仪式以及对鬼魂或灵的扮演,通常作为牛吼器的伴随要素而出现。并不存在任何心理学原理会必然地将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必须被视为在世界某一地区偶然组合成一体,随后作为一个复合体被传播开来。”
Loeb认为,这一复合体包括:“(1) 牛吼器的使用,(2) 对鬼魂的扮演,(3) ‘死亡与复活’启蒙仪式,以及 (4) 通过切割进行的残割。”这与Froese关于如何教授主体—客体分离的模型极为契合。我的贡献在于将Lowie与Froese联系起来,并假设该仪式可能使用了蛇毒。
Lowie是美国西南地区的专家,而霍皮人的牛吼器仪式对蛇教(Snake Cult)尤为重要。下面是一幅霍皮人“蛇舞者”的肖像,他身着礼仪服饰,挥动牛吼器。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Hopi Indian in ceremonial dress whirls a bullroarer decorated with a snake
为什么他们被称为蛇舞者?因为他们真的与蛇共舞,如这张20世纪早期的照片所示: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是的,那些是响尾蛇。显然,没有人因此丧命,因为女性会制作一种传统的抗蛇毒剂,并在庆典前饮用(让人联想到因陀罗在与原初巨蛇Vritra交战前饮下一种饮料)7。
这些实践的古老性可由距今数千年的岩画艺术得到证明。整个地区的岩刻图像描绘了与蛇共舞的人物形象,在某些案例中,如犹他州莫阿布,还出现了口中含蛇的人形图像。这些古老图像表明,与毒蛇的仪式化接触,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是美洲原住民灵性传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埃琉西斯秘仪(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酒神庆典参与者(迈那得,Maenad)发髻中盘绕着一条蛇。希腊,公元前490–480年。
如果我写作于Lowie的时代,就不必介绍秘仪了。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就意味着要理解希腊人,而理解希腊人就意味着要了解秘仪。但那样的时代早已远去,因此我借用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话。罗马人尽可能“复制粘贴”了希腊文化。回顾这一努力时,西塞罗对埃琉西斯赞叹不已:
“在我看来,你们的雅典在其为人类生活所创造并贡献的诸多卓越而神圣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一项能胜过那些秘仪。正是通过它们,我们从粗野野蛮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人之状态,并被教化为文明人。”8
你或许听说过希腊悲剧。这一艺术形式就发源于秘仪。你或许听说过马可·奥勒留。他是埃琉西斯的入秘者,当神庙被洗劫后,他重建了它,并以一尊胸口刻有蛇形的自画像半身像纪念自己与秘仪的关联。
神庙的秘密仪式以狄俄尼索斯的故事为中心,围绕死亡与重生的主题展开。神话讲述年轻的狄俄尼索斯如何被泰坦用四件物品引诱至死,我们必须假定这些物品也出现在仪式中:一条蛇、一只苹果、一面镜子和一只牛吼器。
古典学家Carl Ruck创造了“entheogen”(字面意为“内在之神”)这一术语,用以描述在宗教情境中使用的致神性物质。他数十年来一直研究地中海地区的秘仪宗教。他主张,在这些死亡与重生的仪式中,广泛存在使用蛇毒的实践。
“人们通过‘挤奶’蛇来获取其毒液,将之作为精神活性毒素,既用作箭毒,也在亚致死剂量下作为涂抹剂,以进入神圣的狂喜状态。”
这项研究发表于2016年,但早在1976年,女性主义考古学经典著作《当上帝是女人》(When God Was a Woman)就用数页篇幅推测,蛇毒在大母神崇拜中被用作药物,并同时引用了埃琉西斯与霍皮人的例证。我并非第一个偶然发现这一想法的人,不过我或许是第一个将其与认知进化联系起来的人。
这是一个离奇的事实模式——在我写原始论文时几乎未曾梦想到。19、20世纪,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超越自身的欧洲传统来理解人类处境。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发现,在其他文化的核心,同样存在一个牛吼器崇拜,往往与创世或第一祖先相关,并伴随类似的死亡与重生仪式复合体。最自然的解释是,这一复合体在遥远的过去某个时刻传播开来,甚至可能早于农业革命。《自然》杂志的编辑委员会甚至在1929年持这一立场9。如果这一切还不够,两种最显著的仪式版本——霍皮人与希腊人——都使用了毒蛇。科学通过提出预测来运作。“一个在神话上与人类处境之诞生相关的死亡与重生蛇教”不应如此整齐地嵌入世界历史之中。
结论#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Demeter Gives Her Chariot to Triptolemus。他乘坐由蛇拉动的战车飞越天空,将埃琉西斯秘仪传播至遥远的土地。
目前仍是早期阶段,但随着我们不断收集基因与考古数据,我们会惊讶于在过去5万年间人类大脑发生了多大变化,以及世界各地文化之间是多么深度地交织在一起。直到约1万年前,全球范围内关于完全具备智人心智行为的证据仍极为零散。我认为,这可以通过基因—文化互动来解释。我们知道家犬在过去1.5万年间传播至全球。我提出,一个蛇教也同样传播开来,并携带了“驯化我们自身”的工具包。这个教派核心的秘仪在我们的神话中延续至今。路西法(Lucifer),光明使者,引诱夏娃。女娲与伏羲,中国的第一对夫妻,总是被描绘为半人半蛇。而彩虹蛇(Rainbow Serpent),在时间之初将语言与仪式带到澳大利亚。
我的时间线是:象征性思维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出现,伴随着最初的原始艺术与埋葬行为。然而,“我”这一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以极其破碎的方式被体验,直到更近的时代。随着教授“我”的方法在约1.5万年前随蛇教传播至全球,对“无缝建构‘我’”这一能力的选择压力才开始增强。蛇毒被使用过,但禁食、舞蹈、冥想或其他致幻物质也是可行路径,且在数千年间必然出现过许多不同版本。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我在”(“I am”)是一项被发现的事物,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传播。人们只需教会他人如何获得这一顿悟。一旦这种方法存在,有什么能阻止它的扩散?隔壁那个半清醒的部落?他们会被羽蛇神(Quetzalcoatl)一击致败。
还有许多其他研究我本想纳入。你可知道,在刚果雨林深处,俾格米人的创世神话与《创世纪》高度相似?“我”这一词在不同语系之间的形式远比随机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相似?你是否知道,小麦最早被驯化的地点,正是《创世纪》中伊甸园被描述所在之地?而且这离世界上第一座神庙——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极近,在那里蛇是主要的图像主题,并且牛吼器被用于仪式?我在其他文章中讨论了这些以及更多内容,而最完整的模型呈现在E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中,它加入了性别维度:女性创立了蛇教。最后,如果你在好奇,为何这样的理论会出现在博客而不是人类学期刊上,我在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牛吼器并不为人所熟知。
以正确的方式开启蛇年。愿这一年充满智慧、蜕变与订阅。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女娲与伏羲,中国的第一对夫妻。
另一篇论文发现,单倍群R1b进入乍得的时间线与此相似。 ↩︎
Froese并未明确指出基督教圣礼是残存形式;我只是将其作为最为人熟知的例子。然而,诸如Joseph Campbell这样的神话学家认为,围绕基督复活的仪式是更为字面意义上的死亡—重生实践的残存形式,而这些实践可追溯至农业革命。这正是他那部《世界神话历史图志》(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的全部旨趣:该书从狩猎采集者神话(《动物之力之道》(The Way of Animal Powers))出发,展示农业文化如何改造这些观念(《播种大地之道》(The Way of the Seeded Earth)),并最终在轴心时代发展为现代宗教(《人之道》(The way of Man))。蛇教可以被视为一种论点,即旧石器时代宗教的核心创新,是一种教授“我在”(“I am”)的方法。他们发明了“存在”。今天,所有文化都是对这一观念的变奏。正如《奥义书》所言:“太初,唯有大我,以人之形而存。它反观自身,除自身外一无所见。于是它的第一句话是:‘此即我!’于是‘我’(Aham)这一名称由此而生。” ↩︎
在YouTube上,有数十个类似的粉丝剪辑视频,来自诸如“Spiritual Awakening”之类的账号,标题如“Why I Drank Cobra Venom?”。 ↩︎
或者说是夏娃,也未可知。 ↩︎
Lucifer意为“光明使者”。 ↩︎
另见这篇关于蛇毒机制的最新论文:“因此,可以合理推测,蛇毒诱发的神经损伤与CHRNA7[神经元型乙酰胆碱受体α7亚基]之间存在特定关联。同样,CHRNA1也参与神经发育、神经可塑性以及精神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生。” ↩︎
正是类似的抗蛇毒暗示最初将我引入蛇教这一“兔子洞”。许多在神话中与蛇相关的植物(如苹果、莲花、茴香)都是芦丁(rutin)的极佳来源,而芦丁是一种有效的抗蛇毒成分。 ↩︎
M. Tullius Cicero, De Legibus, ed. Georges de Plinval, Book 2.14.36 ↩︎
“从其分布情况推断,这些特征具有古老的、可能为旧石器时代的起源,而非近期扩散的结果。就牛吼器而言,早期理论应被视为站不住脚。只有在将其使用局限于玩具或魔法用途时,才有可能将其视为在不同地区独立起源。在与启蒙仪式和秘密社团相关的情境中,它总是与某种形式的部落标记、死亡与复活仪式以及对鬼魂和灵的扮演相联系。它对女性是禁忌的,并且无一例外地被表现为灵的声音;但当它出现在启蒙仪式和秘密社团区域之外时,则不具备这些特征。由于在大洋洲、非洲和新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心理学原理会禁止女性看到这一器物,因此不能将其视为独立起源的结果,必须推断它是从一个共同中心扩散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