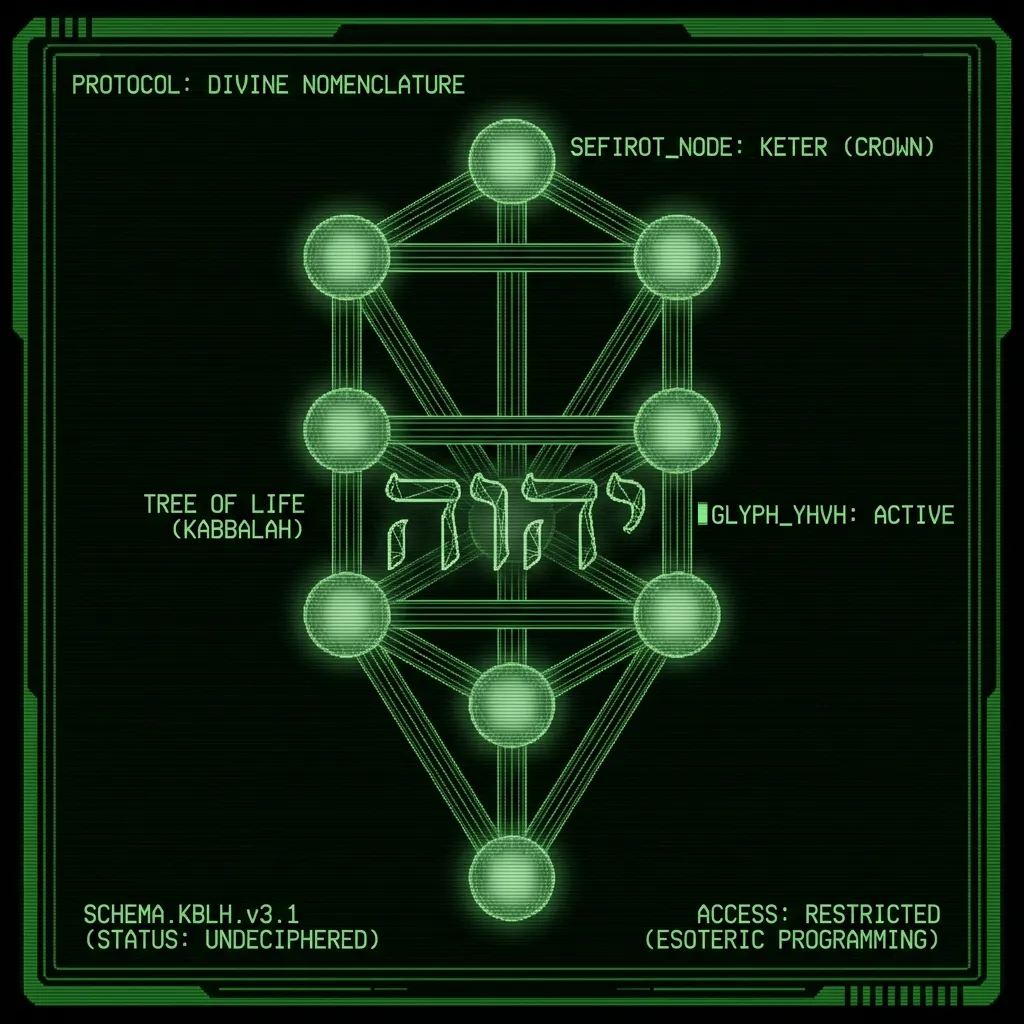From Vectors of Mind - images at original.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MidJourney 6.0
距离上一次给订阅者的推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时候来个近况更新。我现在手上攒着几篇更长的文章,包括 EToC v3;请留意它们。与此同时,会有更多播客节目上线。计划是让播客相对于写作退居次要位置——我更偏爱写作。不过,音频形式非常适合协作性或实验性的想法。即便你是冲着“蛇的内容”来的,我也鼓励你深入看看其他内容。我和 David Stillwell 的访谈,讨论了心理学现状以及 Cambridge Analytica 丑闻,是一个难得的视角切入口。
链接#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The Bayesian Conspiracy#
在 Bayesian Conspiracy 播客中,他们讨论了《The Snake Cult of Consciousness》。整期节目里,他们经常说,“Andrew 大概会说……”而且每次都说对了。他们对我想要呈现的内容有一个准确的心智模型,并且加入了非常精彩的评论。作为准备的一部分,他们让一个带英式口音的 AI 朗读了“蛇教”那篇文章,你可以在这里收听:
Unsong#
我最近读完了 Scott Alexander 的科幻小说 Unsong。他是这样描述这本书的:
“Kabbalah 是真的,所有模式都有意义,世界运行在牵强的类比和文字游戏的组合之上。硅谷的大公司给上帝的名字申请版权并大发横财。国际外交官把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古老冲突转化为美苏代理战争。一位自闭症大天使和他八岁的学徒费力地调试物理定律。一群亿万富翁雇了一艘魔法船去寻找上帝,好告诉祂自己哪里做错了。激进的一元论者小组窝藏着危险的安慰剂恐怖分子。而业余卡巴拉学者 Aaron Smith-Teller,核物理学家 Edward Teller 的远房亲戚(‘不把世界末日带进来并不是我们家族的强项’),发现了一个传说中的上帝之名,并从他家里的电脑上策划了一场迎接弥赛亚时代的计划,结果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发展。”
这本书会让人笑出声来,而在结尾,他确实给出了一个关于恶之问题的答案(这不算剧透)。本博客的读者已经对“如果神秘的犹太教是真的”这类思想实验有了预热,所以我想他们会喜欢这本书。Unsong 让我好奇 Scott 为什么对卡巴拉了解这么多,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讲了更多:
澳大利亚远古史的问题#
我经常随口批评人类学家。为了让我的主要批评更清晰可辨,它其实相当无聊:人类学家已经放弃了宏大理论。总体而言,科学已经被官僚化,资金通常会拨给那些在狭窄议题上显示出边际进展的项目——例如,刻画牛吼器的声学特征。这项工作本身很有趣(我也引用过),但房间里的大象被忽视了:为什么牛吼器会在全球类似的仪式场景中被使用?你需要一个宏大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这类理论已经不再受欢迎。
在牛吼器这个例子中,最简单的解释——扩散——也不再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宏大理论。在化学中,分子会从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同样,诸如仪式乐器这样的观念,会从更复杂的文化扩散到较不复杂的文化。把某种文化界定为“较不复杂”在当代人类学中极不受欢迎。这就引出了我对这个领域的第二个批评:它往往被意识形态裹挟,以至于把地面的事实扭曲得面目全非。
这对任何科学事业来说都是个问题。计算机科学是意识形态化的吗?当然是。比如,你要在基于理论证明的算法和基于经验结果的算法之间做价值判断。或者看一个更显而易见的例子:算法决策的差异性影响。出于根本性的原因,计算机视觉系统在雪地中检测白人、在夜晚检测黑人都更困难。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答案需要来自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
人类学家给流行意识形态太多扭曲真相的空间。对局外人来说,这一点很难理解,因为相关争论往往非常晦涩。通常不值得花力气去弄清事实本身,以及那些决定事实如何被报道和解释的意识形态战线。偶尔,人类学家会试图以显然错误的方式扭曲现实。比如,当人类学家 Kathleen Lowrey1 试图做一场题为《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Why Biological Sex Remains a Necessary Analytic Category in Anthropology》的报告时,这场报告被以极具攻击性的措辞取消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否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立场。而对那些主张“生物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是存在的”的同事进行言论管制,则更加激进。但这在当代人类学中却是主导立场。
需要记住的是,这种程度的扭曲经常被施加到人类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当它触及身份认同时。只不过我们更难察觉,因为我们对牛吼器或澳大利亚的人口迁徙并没有现实世界的体验。成长过程中,我被教导说澳大利亚只被定居过一次,原住民自抵达以来基本保持了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故事干净利落,但问题很多。 read over 100 papers to piece together a more complete vision. 我强烈推荐他写的三篇系列文章。在第三篇中,他引用了一本书中的一段话,恰当地概括了这种状况:
“在轶事层面上,澳大利亚考古学家经常彼此抱怨,全球人类史综述对澳大利亚考古学的处理是多么轻蔑或草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澳大利亚研究者基本上忽视外部世界,假定当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大约在 6.5 万年前来到这里、看见并征服了这片土地,然后,除了大约 3000–5000 年前可能引入了澳洲野犬——一种作为非有袋类动物必然来自别处的犬科动物——之外,一直与外部世界隔绝,直到印尼的马卡桑采海参者在欧洲人出现前不久开始季节性地利用北部海岸线。极其不寻常的是,大多数关于澳大利亚史前史的一般性综述甚至都不会在一笔带过之外(如果有的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最初殖民时期直到全新世早期,这块大陆一直通过陆桥与新几内亚相连。” ~Lapita: The Australian connection, Ian Lilley
我在下一期播客节目中采访了 Lowrey,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