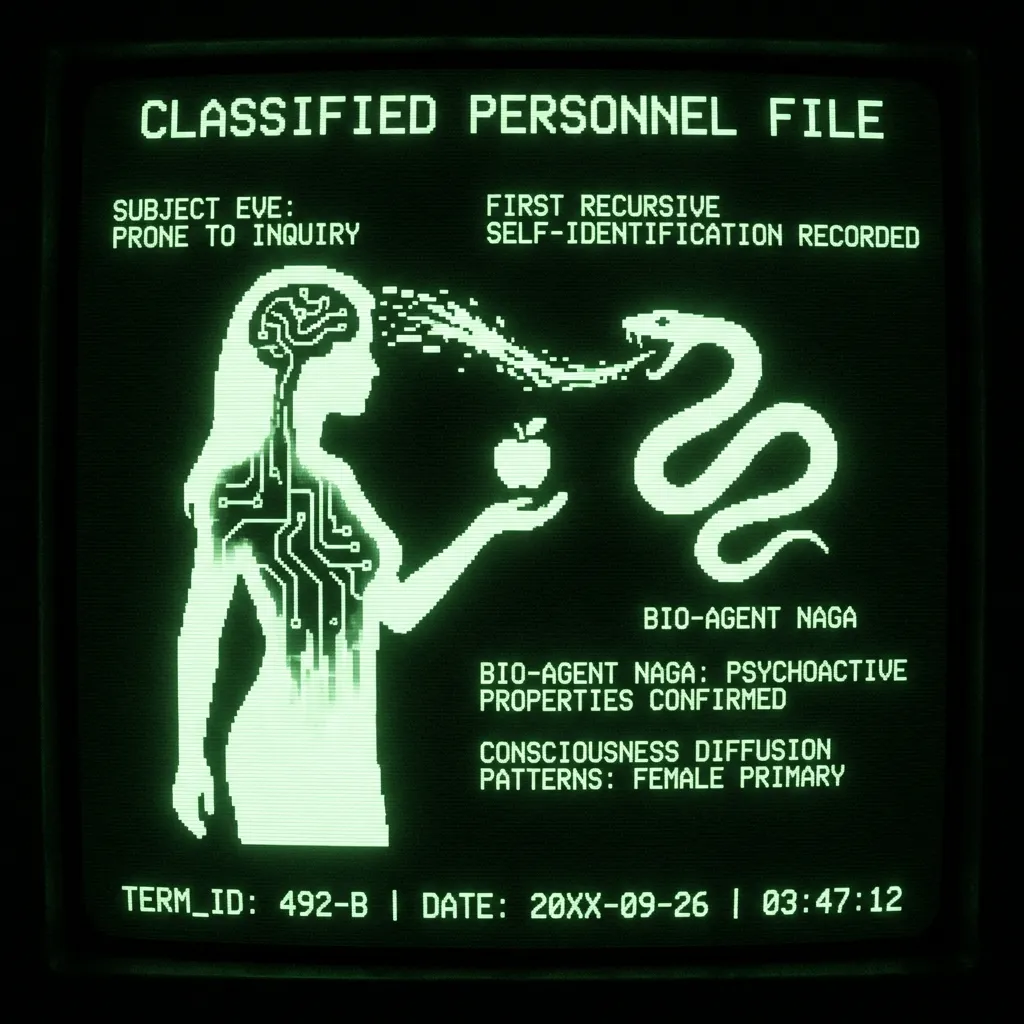摘自 Vectors of Mind —— 图片见原文。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夏娃与蛇》(Eve and the Serpent),1803 年,艺术家不详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创世纪》3:6–7
据某些说法,智人(Homo Sapiens) 约在 20 万年前进化出现。然而,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期里,几乎没有“智慧行为”的证据。石器在数万年间保持不变,意味着无数世代在没有任何创新的情况下生老病死。没有艺术,也很可能没有讲故事。大约在 5 万年前,一种截然“人类”的文化出现了。工具变得更复杂。制作的风格和方法在数百年内就会发生变化,而不是数万年。艺术、宗教和历法被发明出来。从那时起,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许多科学家认为语言大约在这一时期进化而成。这看起来就像是内在生命的黎明。
关于我们何时成为“人类”的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最清晰的怪癖之一,就是对叙事的需求,尤其是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从何而来”的叙事。所有文化都会回答这些问题。达尔文进化论的“丑闻”在于,它违背宗教,用物质原因——自然选择的渐进过程——来解释这些问题。人类不再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而是与兽类同属一棵家族树。我们无疑与其他动物共享一个共同祖先。但这掩盖了一个更深的问题: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也许与黑猩猩共享 99% 的 DNA,但在那些有意义的特质上,人类在类别上是不同的。我们拥有语言和符号性思维。我们天生是二元论者,感觉在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是由某种“精神性物质”构成的。一条狗从未经历过存在主义危机1。这些属性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似乎是二元的:一个有机体要么拥有它们,要么没有。我们是如何一点一点地进化出这些决定性特征的?是否曾经有一段时期,人类只具备“半套”的符号性思维能力?那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是科学中的一个重大未解之谜。
20 万年前的解剖学现代性(anatomical modernity)与 5 万年前的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之间的张力,贯穿于人类起源研究。例如,参见 Michael Corballis 的著作 The Recursive Mind: The Origins of Human Language, Thought, and Civilization。他论证说,递归思维支撑着自我意识、语言、计数以及想象未来。整套“人类组合包”被紧紧缠绕在一个单一原则之上。但时间线却令人困惑。他“确信”,如果把 20 万年前的一个 智人 放到今天抚养长大,他完全可以毫无问题地成为一名律师、艺术家或科学家。他声称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不存在认知差异,但随后又花了好几段文字详细描述,从 4 万年前开始,文化出现了一个“繁花盛开”的阶段,看起来就像递归的出现,也许递归就是在那时进化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乐观的意识形态。“是的,在 20 万到 4 万年前之间没有任何智慧的迹象,但如果一个早期智人在现代学校系统中长大,他会完全正常。进化在区区 20 万年里不可能改变大脑。” 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却贬低了“人类火花”。它暗示,在石器时代,我们如今视为根本性的那些东西,根本没有发展出来。创作艺术和追寻意义的冲动,并非一直存在于我们物种之中,而只是过去 5 万年来人类所处环境的一种“抽搐反应”。如果其他人都停止提出存在主义问题——甚至连乱画涂鸦都不再做——你也会停止。至少,如果一个孩子在那样贫瘠的世界中长大,他会如此。这不仅是对人性的一种黯淡愿景,而且如果语言在 20 万年前就已经进化,那么理解那个时刻几乎无望。时间会吞噬证据。然而,如果语言是在 5 万年前开始出现,我们也许就能重建这个故事。语言性思维的“收尾工作”很可能是在相当近期才进化完成的。
我选择用“灵魂”来框定人类起源。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本可以是 “人类如何进化出一个不可还原的自指性‘我’”,但那样会把我的计划从数千年的思想传统和自然语言的扎根力量中抽离出来。“灵魂”(soul)的含义,是数百万人之间的一种共识:关于自我的本质、能动性的所在以及与神性的连接。当我们在思考“做人意味着什么”时,日常语言提供了一道护栏2。而在这里,它也提供了一个必须被解释的靶子:灵魂从何而来?
鉴于此以及对夏娃的引用,我应当澄清与基督教的关系。我认为,《创世纪》和许多其他创世神话,在现象学意义上,都是对第一个想到“我在”的人的极好描述。根据考古和基因数据,这可能发生在大约 5 万年前。比较神话学家告诉我们,有些故事可以流传那么久;而如果有哪一个故事最有可能被保存千年,那就是我们的“创世记”。
我的论点是:女性首先发现了“我”,然后把内在生活教给了男性。创世神话是关于女性如何将人类锻造成一个二元论物种的记忆。这听起来很奇幻,但我们必然是在某个时刻进化出来的(而那必然是一个奇幻的时刻)。此外,即便是这个观点的弱化版本也依然有趣。例如,我认为蛇毒曾被用于最初的仪式中,以帮助传达“我在”。因此,伊甸园中有蛇,用自我知识诱惑夏娃。即便这些仪式并未真正参与人类进化或我们对意识的发现,如果旧石器时代的某个致幻蛇崇拜同时被《创世纪》和阿兹特克人所记忆,那也将是非同寻常的。我会追这部 Netflix 剧!
在几篇博客文章中,我已经展开讨论:发现“我”会是什么样子,它如何能被传达给他人,为什么女性会成为先锋,它如何能逐步进化,以及这样的过程会留下怎样的文化和基因痕迹。但这些论证散落在不同文章中,而在此期间,我又找到了更多支持证据。例如,早先我曾沉思蛇毒可能被用作致幻剂。事实证明,这在仪式场景中有充分记载,包括在西方文明的奠基者中。
这篇文章从“做人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开始。这对于建立共同框架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这也把“爆点”埋在了后面。最原创的研究是关于全球性的“蛇崇拜”。如果你时间有限,可以从那里开始。或者,如果你更喜欢音频版本,可以收听 Askwho Casts AI 的朗读。(如果你喜欢,考虑在 Patreon 上请他们喝杯咖啡。)
最后还有一件事。理性主义者常常在文章开头标示“应该多认真对待这套论证”。认知状态(Epistemic status):人类起源本质上具有高度推测性,而这是一项超出我专业领域(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之外的热情项目。为写这篇文章,我大概读了十来本书和一百篇论文。理解这套理论的一种方式,是在解读数据时问:“人类最晚可以在什么时候才变得有智慧?”而不是沿用那种试图把这个日期尽可能往前推的体制性偏见3。所以,请谨慎对待,但对这个主题而言,这本来就是常态。
提纲#
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 递归式自我意识。
弱版 EToC,不涉及任何神话引用。递归文化扩散,并在其所到之处引发对递归能力的基因选择。
意识的蛇崇拜:给“嗑药猿理论”(Stoned Ape Theory)装上一口獠牙。
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最初,只有以‘人’的形态存在的伟大自我。它反观自身,却发现除自己之外别无他物。于是它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我!’由此产生了‘我’(Aham)这个名字。” 《广森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1.4.1
“我”是许多创世神话的开端。这一点在上面引述的印度教经文中被明确说出。或者想想埃及的说法:阿图姆(Atum)从原初混沌之洋中升起,是通过说出自己的名字而实现的。圣经中也有回响。亚当和夏娃吃下“知识之果”后变得自我觉察——甚至是“自我意识过强”——并意识到自己的赤裸。对自我的反思能力随之产生了疏离感。亚当再也无法与上帝和自然保持合一,他不得不离开伊甸园。
新约可以被视为这一思想的发展。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开头向《创世纪》致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里的“道”(Word)指的是基督,是对亚当和夏娃堕落所带来疏离的回答。耶稣以自称“我是”(I Am)开始他的传道,这是犹太人对上帝的称呼之一(约翰福音 8:56–59)。这一段经文对许多英语读者而言略过其上,却没有逃过他的犹太听众,他们立刻拿起石头要打死他。他们理解这句话是在宣称:“我就是那位自有永有者,是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现的上帝。”我希望这样运用传递律不算滥用:“太初有‘我是’。”
这些神话教导我们:生命始于“我”;上帝在终极意义上是自指的;而同样的神圣火花也存在于人之内。除了“我”之外,创世神话还将仪式、语言和技术视为区分人和兽的关键。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传说认为,是“文明化的灵”(civilizing spirits)把语言、仪式和技术带给了最初的人类。于是,“梦境时”(Dreamtime)结束,时间开始。同样,阿兹特克人教导说,在现代人类之前,曾有一支由木头构成的人类种族,他们缺乏灵魂、言语、历法和宗教。一场大洪水毁灭了这一“倒数第二代”人类,而真正的人类只因暂时变成鱼才得以幸存。显然,这些神话不能被字面理解。然而,它们的核心却出奇地经得起检验。当科学家回答“是什么使人类独特”时,他们会指向自我意识、语言、宗教,以及我们与时间和技术的关系。许多人甚至认为,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可以用“递归”思维来解释。由此推论,在现实中,这整套“组合包”大致会在同一时间一并进化出来。
创世神话在现象学上的准确性本身并不需要特别解释。叙事景观是竞争性的,只有在心理上最真实的故事才能存活下来,尤其是在宇宙起源这一拥挤的领域。然而,世界各地创世神话中的细节暗示,它们共享一个深埋于过去的共同根源。事实上,它们似乎源自人类首次开始表现出“递归”行为的那个时期。这就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它们并非偶然准确,也不是“尽管自身荒诞却恰好说对了”。它们可能是人类向“智慧”过渡的记忆。
递归是有用的#
自然选择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性状会从父母传给子女。如果某种性状能让父母拥有更多子女,那么这种性状在种群中的比例就会提高。因此,如果消化牛奶或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有用的,这些性状就会在每一代中变得更普遍。既然如此,递归思维究竟能赋予哪些能力?
递归是一种过程,其中一个函数或过程直接或间接地调用自身。换言之,这是一种方法:问题的解依赖于同一问题更小实例的解。这可以像站在两面镜子之间,观看“你的倒影的倒影的倒影”那样简单。最后一个倒影依赖于之前的所有倒影。这个概念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中被广泛使用,用于通过将复杂问题拆解为更简单、更易处理的部分来求解。
在计算机科学中,一个递归函数会把自己的输出再次作为输入来调用自身。通常,每一次后续调用都是一个子程序,其中输入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直到达到某个停止条件。如果这听起来太技术化,不必担心。只要知道,从算法角度看,递归是一种“超能力”就够了。看看下面这个分形图像。存储这张图片最直接的方式,是枚举每一个像素的颜色。但像素很多,而且由于大多数图像内部具有结构,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更高效地存储。在底层,JPEG 使用递归来压缩图像,否则该算法会慢上几个数量级。4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分形是自然的建筑,揭示了塑造我们世界的底层递归模式。”——伯努瓦·曼德博(Benoît Mandelbrot)
对于这张图像,还可以更进一步,因为它是通过一个递归过程生成的。因此,这张图像可以用极少的字节无损编码——只需写出最初生成该图像的递归程序——几行代码即可。不仅如此,你可以对任意一条边不断放大,看到分形在越来越精细的尺度上不断自我重现。递归几乎像炼金术一样,用极少的东西生成极多的结构。用传奇计算机科学家 Niklaus Wirth 的话来说:
递归的力量显然在于:可以用一个有限的陈述来定义一个无限的对象集合。同样,一个有限的递归程序可以描述无限多次的计算,即便这个程序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显式的重复。
但人类不是计算机。大脑是如何使用递归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背离“白板论”的行为主义者,提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约束所有语言。也就是说,人类具有语言本能。正如蜘蛛会织出特定设计的网,人类的认知硬件也被预先“布线”,以学习某种特定类型的语法。这并不是指各语言中变化多端的动词变位规则,而是一种“元规则”:由于大脑的设计,它适用于所有语言。在他与 Marc Hauser 和 Tecumseh Fitch 合著的 2002 年论文《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中,乔姆斯基认为,递归是人类语言能力的关键特征。每一种语言都以递归作为其语法的基础。
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语言学中的递归意味着:句子可以通过自指的子程序来解析。例如,句子“Watson wrote that Holmes deduced the body was in the shed”(华生写道,福尔摩斯推断尸体在棚子里)可以被分成三部分:
X1 = Watson wrote
X2 = Holmes deduced
X3 = the body was in the shed
华生写了什么?要知道这一点,必须先解析 X2,而这又要求先解析 X3。这里存在一个递归层级结构。每增加一个从句,句子的意义就会完全改变,而这样的添加可以无限继续。我们可以在 X1 + X2 + X3 前面不断加上 Jane said that John said that Harold said that…,无穷无尽。即便词汇表是有限的,也不存在“最长的语法正确句子”。递归从有限的积木中撬出了无限。我们当然不会真的说出无限长的句子,但在实践中,这极大地提升了可表达思想的复杂度。普遍语法建立在与分形相同的规则之上。
敏锐的读者此刻可能对潜在的“偷换概念”感到头晕:我们用“递归”来描述所有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同一回事。这一点是公平的,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把多种类型的递归归为一类,完全属于主流观点。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正在检验:在处理音乐、语言、视觉或运动规划时,大脑使用的递归神经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同的5。再看看心理学家兼语言学家 Michael Corballis 的工作。在语言之外,他在其著作 The Recursive Mind: The Origins of Human Language, Thought, and Civilization 中又加入了几种递归“超能力”:包括内省、计数以及思考未来的能力。由于这是对未来的想象,它也意味着创造虚构——那些并不存在的世界。这正是艺术、精神生活以及“人类处境”的开端。
因此,递归是有用的。有了它,人类成为依赖文化的存在,拥有语言本能。但更重要的是,对个体而言,递归是意识的基础。这种双重用途(请原谅这个双关)值得牢记,尽管意识与进化适应度常常被分开讨论。
递归是意识的必要条件#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Silvia 对“见证意识”(witness consciousness)这一冥想技术的描绘。
内省在定义上就需要递归。如果自我感知自身,那就是递归。因此,“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这句话在多个层面上都是递归的。递归语法把两个短语连接起来,而心灵则被指向自身。
笛卡尔推理说,任何事物的真实存在都可以被怀疑,只有一个例外。你伸出手,摸到一张桌子?嗯,有人曾经幻觉出类似的东西。它也许并不存在。唯一无法被他用理性推翻的,是“自我”,因为只要有一个在怀疑的“思考者”,它就必然存在。“我怀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
在这句话中,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递归层面。“我”在静止状态下本身就是递归的,而不仅仅是在感知自身时如此。理解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从“能力”的角度来思考。你的“意识心灵”和“潜意识心灵”之间的分界,是你能否对其进行内省,而不是你此刻是否正在内省。类似地,“我”的边界可以被定义为“能够递归地指涉自身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在任一时刻是否正在执行这种操作”。
可以提出更为精致的论证。Douglas Hofstadter 的经典著作 I Am a Strange Loop 提出,“我”是由与哥德尔用来“击破”数学的那种自指悖论所产生的。论文《Consciousness as recursive, spatiotemporal self-location》中引用了十几篇文献,将递归与意识联系起来,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关于“意识的高阶理论”(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的条目亦是如此。许多聪明人都认为,我们所谓“活着”的核心需要递归。
我们习以为常的“与二元性和时间的关系”,其实都建立在递归的基础之上。在继续往下之前,值得先尝试理解这一点。
自我障碍同时也是主观时间的障碍。那些影响自我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病,也会扰乱时间体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服用迷幻剂来涉足这一领域,它们会产生“自我死亡”(ego-death)。这样的旅程在钟表上可能只有 15 分钟,却主观上像是几十年。一个更日常的例子是“心流状态”(flow state),它似乎会拉长时间。
如前所述,“心理时间旅行”(mental time travel)——思考未来或过去——是有用的。称之为“时间旅行”并不夸张,因为你在模拟未来,从而可以灵活地为之做计划。这不同于本能行为,比如松鼠为冬天埋藏食物。事实上,人类可以利用心理时间旅行来“思考出”对抗本能的行为。人类追随猎物迁徙了无数世代。想象一下最早定居下来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必然对下一个季节有某种概念,并推理出:他们不必再跟着兽群迁徙,因为他们已经种下了庄稼(或有其他替代方案)。
活在当下之外,是一种对物质世界的新型疏离。许多人因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英雄之旅”而认识他——即所有(或大多数?)故事都遵循一个基本模板的观点。这一观点被普及为一系列步骤:英雄通过这些步骤超越自我与社会,然后再重新融入。在坎贝尔的最后一本书中,他描述了所有故事如何从递归中绽放:
在那则出自《广森林奥义书》的古老创世神话中,万有之“原初存在者”在最初想到“我”时,立刻体验到的首先是恐惧,然后是欲望。那里的欲望并不是为了吃东西,而是为了成为“二”,然后繁衍。在这一原初主题的星座中——首先是无意识的合一;然后是对自我存在的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灭绝的直接恐惧;接着是欲望,先是对“他者”的欲望,然后是与“他者”合一的欲望——我们拥有了一组“基本观念”(elementary ideas),用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恰当的术语来说,它们在整个人类神话史中被一再奏响、转调、发展、再度奏响。而作为贯穿这些主题永恒演绎的恒常结构性张力,是那种在“二元意识”与“更早但已失落的合一知识”之间的原初极性张力;这种合一知识仍在逼迫着实现,并且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会在一种“自我消融的狂喜”中突破而出。
叙事以自我意识为前提。这一点在古代就已被认识,并在 20 世纪由坎贝尔和荣格等人进一步发展。有了自指,我们的动物性驱力便化作渴望与想象的分形交响曲6。在“我”之前,没有故事,也不存在所谓“活着”这回事。
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递归是支撑人类最强大竞争优势的基础。在哲学中,人们普遍认为递归是意识的必要条件,至少对于人类这种类型的意识而言是如此。下一节将尝试把效用与主观性编织进一个统一的模型。
最初的自转:关于第一次递归性思维的一些模型#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在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一文中,Steven Pinker 和 Ray Jackendoff 讨论了递归性思维为何会进化出来:“这里的问题不是缺乏可能的进化前身,而是候选者过多。” 尽管如此,他们仍提出了一些可能性:音乐、社会认知、将物体在视觉上分解为部分,以及复杂行动序列的制定。我想再补充一个:驱动递归性思维的,可能是那句 “我在(I am)。”
描述这一顿悟时,我会想到那个盲人摸象的寓言:有人摸到象腿,说它是树干;有人摸到象牙,说它是长矛;有人摸到象耳,说它是粗糙的皮革。和他们一样,我会给出几个相关的模型,希望能描述人类向“智性”(sapience)转变的过程。
第一个模型借鉴了弗洛伊德,将心灵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基本动物本性。最早的细菌必然有类似的东西:比如朝着合适盐度的环境游动。在人类身上,这扩展为对食物、性、庇护所等的需求。超我是人类独有的。它是你对社会期待的模型。别人——无论是被抽象为“社会”,还是具体的人物如_母亲_或_酋长_——的期待。自我同样是人类独有的,它在这两种常常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进行调解。这意味着自我是超我之后才进化出来的。
“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先于递归性的自我意识而出现。在递归之前,超我是由对他人行为与期待的模型构成的,就像现在一样。然而,前递归时代的自我是另一种东西:一个原自我(proto-ego)。原自我同样是一个心智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是对自身心智的模型)。作为调解者,它应该与超我和内感受系统都有良好连接,负责追踪身体的需求(这是本我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我在(I am)”对应于自我变得自指,开始把自身作为输入来接收。自我终于感知到了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
换言之,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自己心智的地图,而这张地图成了“我”这片领土本身。或者用 Joscha Bach 的话说,“我们存在于大脑讲给自己听的故事之中。”这为一个古老问题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答案:语言与意识有什么关系?意识需要自指,而自指反过来又允许完整的语法语言。两者都源自递归。(值得注意的是,词语早在完整语法语言或自我反思之前就已经存在。毕竟,亚当在伊甸园中就已经给动物命名了。)
这个模型的一个缺点是,它让这一转变看起来像是某个“东西”的出现,即自我。更恰当的理解是:这是一个新空间或新维度的发现。我最喜欢的类比有几千年历史,并且在许多宗教中都很常见。随着递归的出现,人类进化出了一只可以感知符号空间的新眼睛。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第三只眼”。正如我们的肉眼让我们得以看见电磁波谱,这种大脑中新出现的自指性结构让我们得以感知符号领域。也就是艺术、数学、(柏拉图式)理念以及未来的抽象世界。
Richard Dawkins 说过,进化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刻。第一个是 DNA 的出现,它标志着生物进化的开端。第二个是模因(memes)的出现。正如基因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来复制自身,模因则通过从一个大脑跳到另一个大脑在模因池中传播。我们接收观念,对其加以改进或变异,然后再传递出去。从长远来看,最好的观念会胜出。在这一点上,人类已经完全依赖于分布在无数人类大脑(以及如今的书籍和计算机)中的高度进化的模因。与物质世界相比,模因宇宙在更大程度上才是我们的自然栖息地。这是“存在于大脑讲给自己听的故事之中”的必然结果。一个能够产生这种“我”的大脑,对模因宇宙拥有特权视角。我们是唯一能够“看见”大多数模因的物种——也就是说,能够持有并感知抽象或符号性观念的物种。第一个想到 “我在(I am)” 的人,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是跌入了一个新的维度。从那以后,我们在天空中建造了城堡,也在地上建造了城堡。人类在物质世界中称王称霸,因为我们是模因生态位中唯一的原住民。
我提出的最后一个模型,是最初把我带入这个“兔子洞”的那个。许多科学家认为语言是在过去 10 万年中进化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内在声音会是有意识思维的核心特征?如果意识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语言又是如何如此彻底地整合进思维之中的?
想象这样一个思想实验:第一句内在声音说了什么?在 Consequences of Conscience 一文中,我推理说,鉴于我们物种的社会性,第一句内在声音可能是一条道德训诫,比如 “分享你的食物!” 但内容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它也可能是在我们某位祖先的无意识注意到鸟儿突然安静下来时说的 “跑!”。问题在于,她会把这第一句内在声音认同为“自己”吗?我认为不会。身份认同是复杂的,需要递归。幻觉则不需要,而且至今仍很常见。这提示我们应当把“递归最初是什么时候进化出来的?”重述为“人类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把内在声音认同为自我?”
在写那篇关于内在声音的文章(Consequences of Conscience)时,我很难传达这一时刻在现象学上的重要性。我意识到,我很难比《创世纪》做得更好,而《创世纪》读起来很像是在描述亚当被教导:他的内在声音就是他自己。在那之前,超我的幻听之声若不是诸神的声音,又会是什么呢?它们向人类发放建议或命令。由此推论,当撒旦说夏娃的眼睛会被打开,她会如同神一样时,他说的是实话。
这就意味着,《创世纪》源自现象学时间的开端。认真对待这个想法,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天马行空的狂想。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惯例。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信息在神话中可以被保存多久,以及人类最早何时展现出内在生活。令人惊讶的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神话可以从大约人类开始做出任何表明递归性思维的事情时起一直存续下来。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自诩科学的人试图把这两点联系起来。这就是这个傻瓜要去做的事。
意识的夏娃理论(E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EToC)#
《创世纪》是否可能是对人类处境之发现的文化记忆,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问题:
一个神话可以存续多久?
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人类”的?
如果这两个时间长度大致相当,那么《创世纪》就可能是我们“创世”的记忆。这两个问题都很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解。我在这里讨论了第一个问题,给出了若干全球性模因的例子,它们最早的证据大约出现在 3 万年前。出于统计学原因,最简单的例子是“七姐妹”。在从希腊到澳大利亚再到北美的数十种文化中,昴宿星团(Pleiades)都被说成是“七姐妹”,尽管肉眼只能看到六颗星。这一差异往往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一位失踪的姐妹。鉴于这一细节,全球各地的“七姐妹”神话必然有共同的根源。这不是一个会独立反复出现的情节。
这七颗星被画在法国 2.1 万年前的洞穴壁画上,也出现在中全新世的澳大利亚,在那里它们也是“梦境时代”(Dreamtime)创世神话的一部分。大多数研究者据此推断,这一神话大约有 10 万年历史。正如我稍后会解释的,没有必要假定远远超过 3 万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就问题 2 而言,在 4–5 万年前的“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之前,没有任何关于递归性思维(包括虚构)的有力证据。那一转变本身存在争议,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但目前,只需要确立一点:主流对问题 1 和 2 的估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叠。我会概述递归文化如何传播的弱版本和强版本。先从弱版本开始,它不依赖任何宗教文本,然后再转向强版本,它把创世神话中的共同细节视为有意义的线索。
弱版本 EToC#
当今人类拥有相当无缝的自我建构。边缘处有裂缝,尤其是当你吸毒、冥想或患有精神分裂症时。但许多人一生都在把“我”视为理所当然,从大约 18 个月大开始。起初,并不会是这样。递归环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虽然存在稳定的构型,但我们的认知线路不太可能从完全没有递归,一跃而成以递归为承重结构的无限循环,而不经过显著的进化。这需要经过多代自然选择,才能在幼年时期实现无缝的自我建构。
想象第一个想到“我在(I am)”的人会很有启发性。现代人似乎在幼儿期就变得自我意识。他们至少能正确使用“我”,通过镜像测试,并且脑扫描不再看起来像是在服用 LSD。我猜,第一个有“智性”的人并不是幼儿,因为幼儿并不特别善于内省,也不擅长心智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有“智性”的人会是一位成年人,她在那一刻之前的一生都生活在一种不加反思的统一状态中。我们称她为夏娃(Eve)。她在顿悟时可能正怀孕或正经历青春期,因为这些时期的大脑重组尤为剧烈,尤其与社会认知相关。无论如何,一旦成年人或青少年获得了“我在(I am)”,自然选择就会推动递归向更年幼的年龄发展。最终,这将年龄压低到约 18 个月。
同时,也会存在对“更具功能性”的递归的选择。这里我并不是指更聪明或更擅长语法,尽管那也是一部分。最清晰的视角是现象学的。灵魂的进化打开了整个灵界,其中大部分都被“鬼魂”所萦绕。最初的人类会更加“精神分裂”,他们并不确切知道“我”从哪里开始,其他想象中的幽灵又从哪里开始。幻听是最著名的症状,但精神分裂症还包括失去行动主体感,以及感觉自己的身体(或某个部分)不属于自己。把时间往前推得足够远,这会是常态。再往前推,就根本没有任何“所有者”。递归作为默认模式的运行有一个平滑程度的光谱。现代的癫痫或精神分裂等紊乱映射到这一光谱上,但与过去存在的变异相比,它们只是轻微的。最初的一千只灯泡按今天的标准看都极其不稳定。意识之光也是如此。正如我之前写过的,中间的进化时期可以被称为“疯狂之谷”(Valley of Insanity)。递归进化得越慢,人类作为“精神分裂人”(Homo Schizo)的时间就越长。
最初一千个想到“我在(I am)”的人,可能都丢失了这条思路,继续在与宇宙合一的状态中生活。如果他们有“意识状态改变”这一概念,那指的会是二元性——自我诞生,而不是自我消解。想象第一个“我在(I am)”能持续一段时间的人。向部落其他人解释这种状况会是什么样?绝对的疯话。就像向一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硅基外星人描述“盐”的味道。没有人理解第一位夏娃,而进化的绞肉机仍在继续运转。鉴于递归极其有用,那些倾向于有“我”顿悟的人,也可能倾向于在其他(原)递归任务上表现更好,比如社会导航或计数,从而拥有更多子女。即便“我”与这些任务之间只有很小的相关性,也足以让“我”的暂时体验在第一位顿悟者之后的数百代中变得更为常见。而且很可能确实存在相关性,考虑到大脑在许多任务上都大量使用递归网络。
在某个时刻,会达到临界质量。足够多的人会体验到“我”——即便只是间歇性地——从而围绕它建立起一种文化。这会为那些能够参与递归文化的人创造一个陡峭的适应度梯度。换言之,递归程度较低的人会死亡或拥有更少的子女。想想在许多千年间,所有这些方式:
语言变得递归化,与之一起的,还有篝火旁的笑话、制作石斧的指令,以及无穷无尽的小部落八卦。
萨满教和整个精神世界只有那些能体验二元性的人才能真正领会。
更复杂的欺骗需要递归。有了二元性,人必须学会戴上面具。其他人则在这种社会技术面前任人宰割:说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套。
递归改变了人与时间的关系,使得对未来的规划更加灵活。这在语言中表现为过去时和将来时,进一步复杂化了语法。
音乐和舞蹈使用递归结构。
这一选择过程可能发生得相当快。假设“无缝的自我建构”的遗传率与精神分裂症相当(约 50%),并且与适应度(存活子女数)的相关系数为 r = 0.1。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因为如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数量只有常人的约 50%(巨大的适应度惩罚)。旧石器时代丛林法则对那些现实感破碎的人可能更加残酷。
把这些保守参数代入育种者方程,递归能力(不间断的功能以及在更年幼年龄的获得)可以每 20 代(约 500 年)提升一个标准差。7 下图展示了在 2,000 年或 5,000 年内,一个群体的递归能力会发生多大变化: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这些钟形曲线代表在 0 年、2,000 年和 5,000 年时群体的递归能力。这与基督诞生无关,只是某个递归开始进化的任意时间点。
在 2,000 年后,这些群体之间几乎没有重叠。作为对比,这大约相当于 8 岁和 12 岁男孩身高的差异。到 5,000 年时,则完全没有重叠。这些是认知上截然不同的群体。现在再看 20,000 年: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在 20,000 年里,进化可以完成大量工作。
构建这样的模型有许多假设,但最主要的一个是:对递归的选择必须持续存在。也就是说,拥有无缝自我建构的人,必须比那些没有的人略微多生一些孩子。这看起来完全合理。r = 0.1 的相关性在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察觉,而递归性思维具有明显优势。记住,Dawkins 说模因的出现是两个伟大进化时刻之一。只有递归性思考者才能接入那口巨大的知识之井。理解递归文化的能力,在传递基因的策略上是彻底“开挂”的。在过去 5 万年中,我们利用这一工具征服了世界,使许多物种灭绝,并在此过程中享受了指数级的人口增长。那时谁在生更多的孩子?那些在递归方面略胜一筹的人。很难想象在那段时间里不存在选择压力。
因此,当我说“进化时间尺度”时,我的意思是:足够长,使得两个群体在递归能力上完全没有重叠。长到在认知上彼此陌生。比如,一个部落的男性在婴儿期就发展出意识,而另一个部落则在青春期才发展;或者一个部落的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 1%,另一个为 10%。结果显示,这个时间尺度可能短至几千年。而这一估计完全在主流答案的范围之内。事实上,Noam Chomsky 甚至说只需要一代人。
Chomsky 和另一位名叫 Andrey Vyshedskiy 的语言学家都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在 5–10 万年前,一次单一突变使递归成为可能,而我们都是那位幸运祖先的后代。这解决了“程度”问题(那是一个像电灯开关一样的单基因),也抹去了“疯狂之谷”。但这几乎肯定是错的。递归函数极易不稳定,如果它能在一蹴而就中被完美解决,那将是极大的意外。数千个基因影响精神分裂症和语言能力。内在生活的进化必然牵涉到同样多的基因。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测序了数百万人,包括数百名史前人类的基因。用群体遗传学家 David Reich 的话说,如果存在某个_“单一关键遗传改变”,它已经“快没地方藏了”_。我写的许多内容都带有推测性,但我看不到任何办法可以绕开这样一个事实:向“智性”的过渡在心理上必然极其怪异。必然有一段时期,内在生活更加破碎。一旦递归开始进化,它作为竞争优势之巨大,足以弥补任何适应度损失,包括诸如“恶魔附身”和丛集性头痛之类的不愉快副作用,这些都会随之一起被遗传下去。人类自我驯化常被描述为变得更加亲社会和女性化。是的,但我认为最陡峭的选择梯度必然是针对“无缝自我建构”的。一个边界清晰的“我”,以及感觉自己掌控着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一切要在幼年就发展出来。
以上是关于_“什么”在进化的模型,现在我们来考虑“何时”_。下面这条时间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熟悉,由一位为 The Conversation 撰稿的进化人类学家整理: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这条时间线承认,人类行为的证据真正开始于大约 6.5 万年前的“伟大飞跃”(Great Leap)。然而,艺术、语言、音乐、婚姻和讲故事却被回溯推到 30 万年前。其推理是:这些是当代人类的文化普遍性,因此必然可以追溯到我们的遗传根源。人类的各个分支已经分离了 30 万年,所以艺术至少必须追溯到那时。正如文章所说:
“我们从 30 万年前南部非洲的人们那里继承了我们的人性。另一种可能性——即每个人、在每个地方,恰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从 6.5 万年前开始同时变得完全人类——并非不可能,但单一起源更有可能。”
鉴于文化可以传播,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如果递归文化在“智性”临界点扩散开来,它会改变所到之处的适应度景观。非递归或半递归的人可以在随后的数千年中进化进入模因生态位。关于遗传隔离的说法也不对。人类最近共同祖先——即所有现存人类都与之有血缘关系的最近一人——远比 30 万年要近。《Scientific American》引用的研究估计这一时间仅为 2–7 千年前。基因的流动性极强。如果存在对递归重要的基因,它们可以从 5 万年前开始扩散。在脚注中,我会讨论 30 万年这一日期的其他问题8。但我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本文的目的在于区分我们的文化根源和遗传根源。递归文化可以先行传播,然后再推动现代人类认知的自然选择。理论上,即便群体之间没有基因交流,这也可以发生。
这位人类学家的表述还隐含了另一个常见假设:一旦出现艺术或其他现代行为的证据,人类就必然已经“完全人类”了。但我一直试图强调的是:递归的进化需要时间。第一个想到“我在(I am)”的人并不像我们。4 万年前的第一批艺术家也不像我们。如果我们设立一个跨时间的收养机构,4 万年前的孩子在现代社会中不会长成律师、医生或工程师。他们会有意识,但在现代城市中很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进化出像“第三只眼”这样微妙的东西需要时间。
理解人类何时“上线”的最佳方式,是查看考古记录以及我们基因组中自然选择的证据。先从考古学说起,图中使用的 6.5 万年这个日期已经相当宽松。这个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看起来是这样的: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维基百科称这是南非 Blombos 洞穴的“可能的岩画”(possible rock art)。年代为 7.5 万年前。在 4.5 万年前之前,没有叙事性艺术。
这并不是递归性思维的有力证据。如果一只喜鹊做出了这样的图案,我会感到惊讶,但这也不会是我见过的动物做出的最聪明的事情。它不需要自我、未来或虚构的概念。把它与从 4 万年前起在从欧洲到西伯利亚各地出现的维纳斯小雕像相比: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威伦多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
关于维纳斯雕像有许多种解读,而所有这些解读都需要递归。最令人动容的一种是:这些雕像可能是自画像——这正是“我”这一发现之后,人们最有可能创作出的艺术形式。此外,大约在同一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明确体现递归的例证。如前所述,计数需要递归。已知最古老的记数棒可追溯到距今 4.4 万年前的南非。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 28 个刻痕,有人提出这可能是某位女性为记录自己的月经周期而制作的,当然也可能是用来记录月相周期。对这些周期的追踪,是在发现主观时间之后,人们最早会发展出的技术之一。最后,印度尼西亚拥有已知最古老的叙事艺术——一幅距今 4.5 万年的洞穴壁画。与其他早期递归例证一样,它与女性也有联系。最早的大量洞穴艺术是手印。通过手指比例可以判断,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留下的。
这些遗物在递归的各个方面都“打勾”:计数、艺术、叙事,以及对自我、二元性与时间的兴趣。在学术文献中,这一转变被称为“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关于我们的心智在距今 4 万至 2 万年之间取得现今形态的观点,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仍是主流。例如,哈佛皮博迪博物馆现任古人类学策展人曾写道:
“在 5 万到 3 万年前这段时间里,现代人从他假想的‘伊甸园’扩散开来,直到通过淹没并取代更古老、更原始的智人亚种的过程,他继承了整个地球。” ~ 《人类的上升》(The Ascent of Man),大卫·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
《Ascent》写于 1972 年,并于 1991 年再版,离现在并不算久。就在 2009 年,心理学家 Frederick L. Coolidge 和人类学家 Thomas Wynn 仍写道:“最简约的解释是,现代执行功能不太可能在距今 3.2 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9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非洲内部深层基因分化的证据使这一观点变得复杂,而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定义(有时甚至不要求具备递归语言)开始流行起来。但再次强调,EToC 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允许人类拥有各自独立的基因与模因根源。证明存在深层基因分化,并不意味着 30 万年前的某个人已经拥有递归的基因禀赋,更不用说稳定的递归能力。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知道 4–5 万年前向行为现代性的转变。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一转变是一个过程。欧亚大陆在距今 4 万年达到的文化水平,直到很久以后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例如,一篇2005 年的论文认为,象征性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在澳大利亚只在最近 7,000 年才有证据可循。10 此外,在全新世之前(距今 1.2 万年),澳大利亚的文化工具组合最接近的是欧洲和非洲的早期与中期旧石器时代(分别为距今 330 万–30 万年与 30 万–3 万年)。换言之,这些工具“过时”了数百万年。从进化时间尺度看,那还是_智人_、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尚未出现的时代。_直立人_打来电话,说他要回他的石器了。11(需要强调的是,作者用这一点来反对“行为现代性”概念。他们认为,鉴于其出现时间太晚,这并不代表一次重大的进化变化。)
更广泛地说,考古学家科林·伦弗儒(Colin Renfrew)提出了“智人悖论”(Sapient Paradox),其问题是:如果人类在 5 万、10 万,甚至 30 万年前就已经在认知上是现代人,为什么直到大约冰河时代结束时,现代行为才广泛出现? 按照伦弗儒的说法:“从远处、在非专业人类学家的眼中,定居革命(距今 1.2 万年)才像是真正的人类革命。”
他并不孤单。迈克尔·科巴利斯(Michael Corballis)提出了递归进化的两个可能时期:40–20 万年前与 4–1 万年前。12 就在去年,语言学家 George Poulos 还提出:“我们今天所知的语言,可能大约在 2 万年前才开始出现。” 同样,语言学家 Antonio Benítez-Burraco 和 Ljiljana Progovac 提出了一个语言进化的四阶段模型,其中递归只在最近 1 万年才出现。按他们的分析,直到那时,人类才表现出足够复杂的行为,以至于需要递归语言。除了社会复杂性,他们还指出,在过去 3.5 万年间,人类颅骨形状在全球范围内向更球形转变。这暴露了“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这一术语的一个怪癖。它被用于距今 20 万年前的人类,但并不意味着“看起来就像现代人”,而是指“具有如今人类常见、并将我们与已灭绝的 Homo 属成员区分开的特征,如纤细的骨骼与减弱的眉脊”。我们的颅骨甚至与 5 万年前都不一样!
如果在过去 5 万年间,大脑曾为递归进行过一次“重新布线”,那么我们应当预期会看到:
颅骨形状的改变
大量与认知相关的新基因突变
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颅骨正变得更加女性化并趋于球形。转向第二个问题,论文《Genetic timeline of human brain and cognitive traits》颇具启发性。下图展示了进入基因库的新基因的分布。注意在距今 3 万年前达到峰值的激增,其中许多是认知相关基因。与考古记录类似,在距今 20 万年前附近并没有太多变化。看起来我们是什么时候进入了一个新生态位,并遭遇了需要新遗传物质来解决的新问题?
[图像:原帖中的可视化内容]“人类表型 SNP”(Human-phenotypic SNPs)是与现代人各种性状相关的基因(严格说是单核苷酸多态性),包括认知和精神特质(如智力、戒烟)。在最近 3 万年间(最左侧三个区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空模型的预测。
作者强调:“含有最近进化修饰(约距今 5.4 万至 4 千年)的基因与智力(P = 2 x 10^-6)和新皮层表面积(P = 6.7 x 10^-4)相关,这些基因倾向于在参与语言和言语的皮层区域(如三角回,pars triangularis,P = 6.2 x 10^-4)中高度表达。”
一篇2022 年的论文发现,在过去 4.5 万年以及 8–4.5 万年间,与大脑和行为相关的基因存在强烈选择信号。他们认为这些是人类离开非洲后,为应对沙特阿拉伯相对寒冷环境而产生的适应:
“虽然神经功能最初看起来令人惊讶,但这一观察很可能主要与神经系统和大脑在协调、整合并随后调节多种生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关,而这些过程会受到寒冷环境的影响。”
人们不禁要问,沙特阿拉伯是否真的冷到足以引发如此显著的大脑功能变化。13 他们也提到,“颇具挑衅性地”,这可能表明与社会性相关的认知进化。14(我还要补充说,这也可能与递归有关,而递归的最早证据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
因此,EToC 的弱版本认为,递归文化的传播改变了适应度景观。递归并非总是均匀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一个大致的时间线是:在 5–10 万年前存在一些“二元性时刻”15,而在 5 万年前,当递归在心理上被整合得足够充分,可以开始围绕递归技能构建文化时,递归才真正被“投入使用”。鉴于不久之后在全世界都能发现递归,这种文化必然曾经传播开来。在那时,“我”未必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存在。个体与其内在声音的关系可能千差万别。在某个时间点,也许相当晚近,自我无缝建构成为全球的常态,而这种建构的中断如今被病理化了。
大部分选择压力应当集中在过去 5 万年间。在尚未出现象征性文化之前,如何会对象征性思维产生选择?一开始,选择必然是逐步发生的。它一定是从“几乎不具递归能力的人类”产生“几乎不具递归特征的文化”开始的。鉴于递归带来的诸多问题,这种状态也许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均衡。到了某个文化复杂度的临界点,递归思维就会成为“入场券”,从而形成陡峭的选择梯度。
关于“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所呈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综述。在众多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我选择强调递归(而不是例如“象征性思维”),是因为它自然地展示了人类转变既是实践性的,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我们进化出了“灵魂”,而这使我们得以征服世界。大多数关于自我驯化的叙述强调的是相处与非攻击性,即狼与狗之间的差别。然而对人类而言,这一变化是范畴性的。Homo Sapiens 意为“思考的人”。非递归的人类并不具备“智性”。他们与时间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与我们相比,就像水之于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绝对独一无二的。这并不算什么新贡献,因为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这样说。我的贡献在于,我认为这一转变如何可能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展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对“是什么使人类特殊”的(非常不完整的)模型,并不是后续论证的必要前提。如果你不同意递归,可以用“象征性思维”、“语言”、“高阶思维”或你偏好的“灵魂”定义来替代。唯一真正的要求是:它必须是一种“相变”。
许多研究者认为,大约在 5 万年前发生了某种生物学变化,而语言(或递归)是候选名单上的重点之一。我与他们略有不同之处在于,我更强调基因—文化互动,以及这一过程可能持续的时间之长。即便在 5 万年前已经存在一些“具备智性时刻”,完全现代的心理学也可能要晚得多才出现。EToC 的弱版本假定,“递归文化”是在过去 5 万年间传播开的。为了捍卫这一观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明确指出那究竟是什么。EToC 的强版本则认为,大体上是女性最先理解了“我在”(“I am”)。后来,她们发展出帮助获得这一顿悟的迷幻蛇仪式,并使这些仪式得以传播。男性视角则保存在许多创世神话中,包括《创世纪》。这就是我为何强调递归的现象学含义。值得反复讲述的故事,关乎的是意识的改变,而不是技术。因此,如果递归是在口述传统仍可及的时间范围内进化出来的,那么最受敬重而被传承下来的,将是与时间、自我意识、能动性和二元性有关的变化,而不是更复杂语法或石器工具等功利性关切(尽管它们的引入也被记住了)。
意识的蛇崇拜(The Snake Cult of Consciousness)#
[图像:原帖中的可视化内容]《蛇》(The Serpent),出自系列《夏娃与未来》(Eve and the Future),作品 III,1880 年,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纪》3:5
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而不是一位反复无常的上帝在颁布自相矛盾的戒律。一旦夏娃将自己视为一个行动者,并将她脑中的声音视为自己的声音,她就再也无法停留在幸福的无知之中。她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也有人提出过这种解读。朱利安·詹恩斯(Julian Jaynes)甚至将其与对内在声音的认同联系起来。但蛇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乘坐时光机去拜访正处在递归门槛上的人类,你能教他们关于“我”的概念吗?你会尝试什么?我会把“我”嵌入一个恐怖仪式中——一个“唯一的出路在内心”的密室逃脱。这会拉动许多生物学杠杆,包括迷幻药,因为它们有助于“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其急性效应包括打开心智、使新奇想法得以产生。尤其受影响的是与内省和意识相关的功能。
一个主要以“自我解体”(ego death)著称的药物类别,竟然可能参与“自我诞生”,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所提出的机制更像是一次“脑重置”:在此期间,入门者会产生许多新想法——希望其中包括“我在”(“I am”)——随后是数周的大脑可塑性增强期,在此期间这些想法可以被整合。这并不是我的创见。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在他的著作《诸神的食物:对知识原树的探索》(Food of the Gods: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Tree of Knowledge)中提出了“嗑药猿理论”(Stoned Ape Theory)。
对麦肯纳而言,意识与迷幻药之间的关系是实践性的。当他“旅行”(trip)时,他看到意识在自己的心中被建构。他最精彩的阐述之一,是关于他所描述的“自我变形的机器精灵”(self-transforming machine elves)——由语言构成的奇幻生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超空间里会有一个无形的句法智能在上语言课。但这确实、一贯地,似乎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基于他在超空间中的“学业”,他认为语言是意识的基础,而迷幻药可以帮助获得意识。
麦肯纳认为,“诸神的食物”是裸盖菇素蘑菇。但它们在宗教史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事实上,一个更好的候选者就在《创世纪》本身:蛇。16 它们的毒液是一种迷幻剂,含有大量神经生长因子。不仅如此,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跨越进化时间尺度,一直被当作赋予意识的对象来崇拜。我提出,最初的“知识之果”其实是蛇毒。
本节从化学层面展开调查,然后沿时间倒流,从现代蛇毒仪式到古代,再到石器时代。
作为“致神剂”的蛇毒(Snake Venom as Entheogen)#
[图像:原帖中的可视化内容]阿兹特克创世神羽蛇神(Quetzalcoatl),从他头上伸出的蛇身布满眼睛。这幅图装饰着特诺奇蒂特兰一座神庙的门楣。我是在度假撰写“蛇崇拜”一文时拍下这张照片的。一旦你认识了“宇宙之蛇”,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很久以前,毒液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它夺走了我的生命,却给了我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萨古鲁(Sadhguru),《我为何喝下蛇毒》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古典学家卡尔·拉克(Carl Ruck)创造了“致神剂”(entheogen)一词(字面意思为“内在之神”),用来指那些用于诱导改变意识状态的致幻物质。重要的是,这并非任何形式的意识改变;它们必须被用来接触“内在的神性”。大多数文化似乎至少有一种偏好的致神剂,比如鸦片、大麻、古柯叶、伊波加根、鼠尾草、死藤水、裸盖菇素蘑菇、槟榔、金合欢或蟾蜍毒液,仅举几例。往往被遗漏在这一清单之外的是蛇毒——这是文献中的一个明显空白,我希望在此加以弥补。
第一个问题是化学层面的:蛇毒能否作为致神剂发挥作用?已有少量论文——足以支撑一篇综述文章——讨论蛇毒作为娱乐性药物的使用。这些病例报告与裸盖菇素蘑菇的情况类似。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毒液由街坊的耍蛇人通过毒牙直接注入患者舌头静脉。仅一次剂量,患者就报告改变了长期根深蒂固的行为。在十年酗酒与阿片类药物依赖之后,他在“亲吻眼镜蛇”后立刻戒掉了这两种成瘾物。Vice 也拍摄了一部关于这一现象的印度短纪录片,以及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个案。
迷幻药会刺激神经生长因子(NGF)的生成,从而提升大脑可塑性。因此,如果你想像 Michael Pollan 所说的那样“改变你的心智”,迷幻药是极佳的工具。现代医学正处在一波迷幻药热潮中,这类药物几乎被用于测试治疗所有精神疾病。
蛇毒不仅仅是刺激 NGF 的生成;它还“自带”NGF。20 世纪 50 年代,实验室从小鼠脑肿瘤中提取 NGF。当使用蛇毒来处理这些肿瘤时,所得 NGF 的效果要强得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独的蛇毒就含有的 NGF,其效力是肿瘤来源 NGF(此前的最佳来源)的3,000–6,000 倍。
这种诱导的可塑性不仅是急性的,也不仅仅与 NGF 有关。一篇近期论文认为,蛇毒可能成为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基石:“印度眼镜蛇 N.naja17毒液中的一个组分,与神经生长因子并无显著相似性,却被证明能诱导持续的神经突生长(neuritogenesis,即神经元之间连接的生长)。” 目前它正被研究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以及抑郁症。这令人鼓舞,但现代医学仍然非常年轻。大部分潜力仍未被发掘。一篇近期论文写道:“蛇毒可以被视为由许多小型药物组成的库,其中每一种‘药物’都具有药理活性。然而,目前被鉴定和表征的毒素还不到 0.01%。”
接下来是给药方式的问题。我不确定,当毒液注射在舌头上,或像萨古鲁那样混入牛奶口服时,NGF 是否具有生物利用度。这篇论文发现,即便不通过注射,舌头也是穿越血脑屏障的极佳位置。但“剥猫皮的方法不止一种”,而“喷火龙”的方式就更多了。古典学家 David Hillman 提出,在希腊神庙中,蛇毒混合物是通过肛塞方式给药的。给药方式似乎并不是限制因素。
最后一个标准是:毒液是否在灵性场景中被仪式化使用。YouTube 上有数十个印度上师萨古鲁谈论他为何喝下蛇毒的视频。用他的话说:
“如果你懂得如何利用它,毒液会对一个人的感知产生重大影响……它会在你和你的身体之间带来一种分离……它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会让你永远分离。” ——《毒液如何作用于你的身体的未知秘密【实践体验】》
毒液的灵性用途并不限于这位上师。接下来的章节将考察世界各地的神话与考古证据。结构上将按不断扩大的半径展开:原始印欧语文化、欧亚与美洲,然后是全球范围。
原始印欧语文化(Proto Indo European)#
“人们挤蛇取毒,将其作为精神活性毒素使用,既用作箭毒,也在亚致死剂量下作为药膏,以进入神圣的狂喜状态。” ~卡尔·拉克,《勒耳那九头蛇的神话》
[图像:原帖中的可视化内容]得墨忒耳(Demeter),出自 1817 年出版的《厄琉息斯秘仪论》中的一幅版画
罗马人几乎是“复制—粘贴”式地吸收了希腊文化。回顾这一努力时,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对厄琉息斯秘仪赞叹不已:
“在你们雅典为人类生活所创造并贡献的诸多卓越而神圣的事物中,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那些秘仪更好。因为通过它们,我们从粗野野蛮的生活方式被转化为人之状态,并被文明化。 正如它们被称为‘入门礼’,在事实上,我们从中学到了生活的基本原理,并掌握了不仅是快乐生活的基础,也是带着更好希望去死的基础。” ——M. 图利乌斯·西塞罗,《法论》(De Legibus),Georges de Plinval 编,第 2 卷 14.36
厄琉息斯秘仪是希腊关于死亡与重生的典型庆典。它讲述了珀耳塞福涅被掳至冥界,以及她的母亲得墨忒耳悲痛欲绝、四处寻找她归来的故事。在这一叙事的核心,据说隐藏着生命的秘密。或者用希腊诗人品达的话说:“有福之人,曾见此等仪式,便下入空洞大地;因为他知晓生命的终结,也知晓其神赐的开端。” 至于在生命的开端究竟揭示了什么,则仍是一个谜。那是一个“秘仪教团”,泄露其秘密的惩罚是死刑。但更重要的是,语言似乎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向来能言善辩的荷马,在描述时也退缩了:“对神的巨大敬畏使声音哽咽。” 在厄琉息斯发生的一切,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线索。1978 年,拉克的《通往厄琉息斯之路》在古典学界引发丑闻,他在书中论证,入门仪式的核心是迷幻性的。布赖恩·穆拉雷斯库(Brian Muraresku)在其畅销新书《不朽之钥:无名宗教的秘密历史》(The Immortality Ke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with No Name)中重新审视了这一论点。(可参见萨姆·哈里斯的访谈。)穆拉雷斯库将那句承诺——“如果你在死前死去,你在死时就不会死”——解读为由真菌诱导的自我解体(ego death)的隐喻。作为一名工程师,我从机械角度思考这些可能性。迷幻药是一种强大的认知工具,最强大的宗教技术会借助它们的魅力,这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就厄琉息斯的致神剂而言,还有更好的候选者。
在公元二世纪,皇帝马可·奥勒留被引入了秘仪。他据说是唯一一位被允许进入主神庙至圣所的非祭司人士。作为皇帝,他在公元170年神庙几乎被蛮族科斯托沃克人摧毁后对其进行了重建。他的半身像安放在庭院中,胸前饰有一条蛇。
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也是一名入秘者,他的许多戏剧都涉及秘仪。在其中一部作品中,他似乎“飞得太接近太阳”,几乎因泄露过多秘密而被处死。可以参考希尔曼的解读。
“在古代先知从冥界召唤像阿勒克托这样的灵体之前——这一神秘实践被称为招魂术(necromancy)——他们会先祈请巴克科斯,即狂喜之舞之神。对这位神秘教派神祇的崇拜,在古典文学与艺术中以多种名号出现,如狄俄尼索斯、布罗弥俄斯与扎格柔斯,并与操弄欧洲角蝰(Vipera ammodytes)相关……似乎赫卡忒、普里阿普斯以及得墨忒耳/珀耳塞福涅的女祭司们参与了蝰蛇毒液的摄取。[埃斯库罗斯几乎因在其关于俄瑞斯忒斯的戏剧中泄露厄琉息斯秘仪的秘密而被处决。其中一部戏剧(《奠酒人》)包含一个关于‘雌龙’的梦境,在梦中,她的乳汁被注入了蛇的毒液。]……其中一些女祭司甚至被称为‘雌龙’,并参与了对人类凡性进行‘烧除’的过程。”
直接引文,含“[]”,出自书中章节《Drugs, Suppositories, and Cult Worship in Antiquity》(《古代的药物、栓剂与祭祀崇拜》)
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曾亵渎秘仪,希尔曼在另一篇论文中将此与蛇毒联系起来,该文讨论了“雌龙”/drakaina:
“Drakaina,或 δρακαινα,据说通过将药物混合/制备为可饮用或可食用的形式来获得其力量。有许多具名的 Drakainai,其中最著名者之一是克吕泰涅斯特拉。阿里斯托芬因在其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三部曲中亵渎(泄露)秘仪而遭到指控。在《奠酒人》中,埃斯库罗斯记载,Drakaina 在被蛇/龙咬伤胸部后,调制并施用了一种由血与乳组成的混合物(514行及以下)。俄瑞斯忒斯甚至描述了他自身的‘蛇化’或向龙的转变。(第549行:ἐκδρακοντωθεὶς δ᾽ ἐγὼ,“我自己也已将那条龙引出。”)
……
龙之女祭司进入一种狂喜或巴克科斯式的疯狂状态,在此期间,她们声称通过操控由‘暗星’所产生的时空扭曲‘波动’,来体验并影响跨维度的力量或‘daimones’(恶魔)。希腊人用 ἔνθεος [entheos,字面意为‘内在之神’] 一词来描述这种由星辰引发的奇异狂喜,且神秘主义者声称,这是一种在入秘者‘胸中显现内在之神’的过程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明确指出,秘仪使用蛇毒作为致神剂(entheogen),并提供了数十条一手文献证据。18 尽管如此,能有第二种意见仍然很好,这一次是关于德尔斐神谕(那里的大祭司被称为Pythoness):
“苏族人相信,如果一名年轻、正在跳舞的男子被蛇咬而未死,他将经历一次宇宙性的觉醒。(自古以来,舞蹈被视为对神秘体验的狂喜摹拟,并且至今仍被视为揭示秘仪的途径。)在德尔斐,人们舔食蛇毒以诱发恍惚。甚至有些科学家也证明,他们在被蛇咬后经历了改变的意识状态,见到幻象并感到自身拥有巨大的能力。” Drake Stutesman, Snake, 2005
我们稍后会回到蛇之舞。就目前而言,古希腊人使用毒液作为致神剂这一事实,似乎在至少某个古典学子领域中是常识。19 至少,各种神庙中饲养蛇这一点是有充分文献记载的。20 而且,尽管这可能是耸人听闻的传闻,约公元200年皈依基督教的埃及异教哲学家克莱门斯写道,秘仪包括献给夏娃的蛇之狂欢。21 无论如何,鉴于秘仪可追溯至史前时代,审慎之举是去考察“姊妹文明”,以寻找蛇毒被用作致神剂的佐证。
在16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商人菲利波·萨塞蒂注意到,梵语中“神”(God)、“蛇”(serpent,!)以及某些数字的发音与他的意大利语母语相似。由此诞生了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PIE)假说:印度与欧洲同属一个文化源头,在遥远的过去共享共同的根。此后几个世纪中,没有任何史前族群像他们一样受到如此多语言学与考古学的关注。一般认为,PIE 人民生活在距今6–9千年前、黑海一带的某个地区。他们的后裔扩散至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将其语言、宗教与习俗一并带去。如今,全球 46% 的人口以某种 PIE 语言为母语。
在确立这一联系之后,我们从希腊转向印度,以三角测量的方式考察 PIE 人群中毒液使用的情况。在那里,启蒙之饮被称为 Soma,它同样在神话中与蛇和乳汁相关联。
“蛇(常象征女性)执行一种炼金术,而女性则通过将血转化为乳汁来执行这种炼金术。在村落仪式中,人们将乳汁喂给蛇;蛇随后将其转化为毒液,而毒液又被 Soma(或由掌控 Soma、药物与蛇的萨满)化解。瑜伽士在体液动力学上与母亲相反,他们饮下毒液,将其视为 Soma,从而获得对蛇的力量。瑜伽士还可以饮下毒液并将其转化为精液,并且他可以通过激活那条(有毒的?)盘绕的蛇女神昆达里尼,将自己的精液转化为 Soma。” 《Karma and Rebirth in Classical Indian Traditions》(《古典印度传统中的业与轮回》),温迪·多尼格·奥弗莱厄蒂,1980年,第54页。
再一次,蛇毒与乳汁在象征层面与生命本身纠缠在一起。这一主题弥漫于印度宗教之中。佛陀在获得觉悟之后,被那伽王庇护以免遭风暴侵袭。而且,那伽启蒙并非死去的宗教。饮毒的萨德古鲁拥有数百万追随者,并热衷于复兴涉及蛇的秘传仪式(包括蛇)。在 YouTube 上有许多他的视频,讨论这些仪式的意义,其语言完全符合致神剂话语。而且,与埃斯库罗斯一样,他将蛇毒与乳汁结合使用。我认为尚无人提出“蛇毒 Soma”这一 PIE 传统的论点,尽管在希腊与印度的神圣仪式中,这似乎都有充分记载。(或者,正如我们稍后将讨论的,Soma 也可能是在人与蛇相遇前服用的抗蛇毒血清。)
但我的论点并非关于原始印欧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也不是关于古希腊的自我之死,而是关于自我之进化起源。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欧亚大陆与美洲#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乌纳斯金字塔中的墓室,其上刻有金字塔文。这些文本包括神话与咒语,用以帮助亡者通往来世。对于使用桌面端的读者,这里有一个很酷的墓室 3D 模型。
金字塔文是世界上最早的宗教书写文本之一,可追溯至埃及古王国,大约距今4,500年。它们由大量咒语、祈祷与咒文组成,刻在萨卡拉金字塔及石棺的墙壁上,旨在保护并引导法老在来世的旅程。金字塔文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埃及人宇宙观、创世观与神祇观的宝贵洞见。
与许多其他传统一样,埃及人认为最初只有混沌,常被表现为一片大海。此前,我曾提及一个埃及传统,其中阿图姆通过说出自己的名字从原初之海中显现。下面这段文字则反映了另一种传统,即首位存在者是 Neheb-ka:
“我是原初洪水的流溢,是那从水中涌现者。我是那条拥有众多盘绕的‘属性给予者’之蛇。我是神圣之书的书吏,此书述说已然发生之事,并促成尚未发生之事。” ~ 金字塔文 1146,埃及,公元前2500年
Neheb-ka 被译为“属性的给予者”(Provider of Attributes),但也可以理解为“给予 Ka 之物”或“驾驭/套缰 Ka 者”,其中 Ka 指“灵、魂”或“二重身”。就这样,真真正正被刻在石头上:灵魂最初是由一条蛇所驾驭。通过它们,人被造为“双重”。至少,埃及人是这样认为的。
下方的图38取自罗伯特·克拉克的《Myth and Symbol in Ancient Egypt》,显示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六世统治时期,在那里,“时间”与“形态”被描绘为从宇宙之蛇中涌现。(记住,对时间的体验直接源自递归。)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在古埃及,智慧与感知常由蛇来象征,甚至由蛇赐予。例如,Neheb-ka 将拉之眼22赐予法老: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一幅 hypocephalus(头下护符)下部场景。Neheb-ka 将一只拉/荷鲁斯之眼呈献给明神(Min)。瓦吉特以拉之眼为首部形象,站在牛形的哈索尔身后,向其递出一朵莲花,而哈索尔则面向荷鲁斯的四子。颇为奇特的是,这一场景已成为摩门教经典的一部分,因为约瑟夫·斯密曾购买埃及文物并对其进行“翻译”。
但回到当前的主题,即在美洲与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蛇之神话的共同根源。希腊与印度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它们都源自距今6–9千年的 PIE 文化。再往更久远的年代追溯则会遇到许多方法论问题。然而,蛇之神话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这里,人们接受规模更大、时间更深远的系统发育谱系。如何调和埃及、希伯来与 PIE 传统中赋予生命的蛇,与例如中国的观念?下图是创世女神女娲与其配偶伏羲,二者以蛇身相缠: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中国创世女神女娲与其配偶伏羲。这对神祇常被描绘为一对缠绕在一起的蛇。此画出土于新疆,可追溯至唐代(618–907年)。与这些印度的缠绕那伽颇为相似。或与埃及的塞拉皮斯与伊西斯相似。
19世纪80年代,A. W. 巴克兰小姐注意到白令海峡两岸蛇崇拜的相似性,并主张蛇崇拜与太阳崇拜、农业、纺织、制陶与金属工艺一道,随着最早的迁徙者从欧亚传播到新大陆。一百多年后,比照神话学家迈克尔·维策尔在谈到蛇时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种创世宇宙论在距今4–1.5万年的欧亚地区形成,随后传播至新大陆。他从中国、夏威夷、中美洲、埃及、希腊、英格兰、日本、波斯与印度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材料,提出这一原始创世神话包括屠龙情节,且常借助某种“天界之饮”,如 Soma。在完成此举之后,人类被赐予(或窃取)了文化:“只有在大地被龙之血液所施肥之后,它才能孕育生命。”23
他的方法是比较性的;日本、希腊与墨西哥现存神话之间的相似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必然共享一个古老的根源。为了理解他的意思,让我们回顾一些史前例证,并特别关注致神剂的使用。
在约公元500年的德克萨斯,一名男子吃下一条响尾蛇,连同毒牙、鳞片与尾响一并吞下。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并分析了他的粪便(呃……粪化石)。这一行为被解读为仪式的一部分,因为人们通常不会吃毒牙或尾响。此外,该地区的创世故事中充斥着长角或羽蛇,而根据洞穴艺术,这一传统似乎可追溯数千年。例如,参见下加利福尼亚的“蛇洞”,其年代为距今7,500年。洞中有一幅长达八米的壁画: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这纯属我的猜测,但请注意,人形在被吞噬之前要么是赭色,要么是黑色,而在被吞下之后则变为二元,兼具两种颜色。所有动物则仅为赭色。Neheb-ka 的一张面孔,将灵魂与身体捆绑在一起?
布拉德肖基金会补充道:“该遗址岩画所呈现的母题与创世神话相关;以及死亡与生命和季节的周期性更新。长角蛇这一核心形象遍布整个美洲大陆,并在若干原住民文化的世界观中持续存在。” 这一传统的某些方面在长达7,000年的时间里延续至阿兹特克时代: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羽蛇神奎兹尔科亚特尔的创世形象,出自《特列里亚诺-雷门西斯抄本》。德克萨斯的吃蛇仪式是一个有趣的反转:与其说是创世之蛇吞噬你,不如说是你吞噬创世之蛇。
或者,__看看在今天犹他州与科罗拉多州发现的岩画。科罗拉多高原上的这位蛇萨满被测定为24距今5–9千年: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想看更多十余幅蛇萨满图像,可参见这位摄影师的作品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图片来源这里与这里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或者这幅出自犹他州巴克霍恩峡谷岩画板的作品: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注意这条有角之蛇那对小小的“霸王龙”前肢。可爱极了。
好,再看一幅: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迷宫旁的一条双头蛇。出自犹他州的Notch Panel
迷幻,不是吗?最后这幅图尤其有趣。还有什么比一条盘旋的双头蛇进入迷宫更适合用来表现一次由毒液引发的旅程?同样的符号在欧亚大陆也很常见,那里迷宫长期被用作内在探索的隐喻。例如,下面这幅由新时代艺术家采用的图案: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Pinterest 上的说明文字写道:“蛇是大女神的象征,代表转化与疗愈、整体性的能量以及女性的灵性觉醒之火。”该设计源自一枚希腊钱币。
在埃及,“二重身的给予者”Nehebkau 有时被描绘为双头蛇。再次引自克拉克: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
我并不一定在暗示新旧大陆之间的迷宫或双头蛇存在系统发育上的关联。使用毒液作为致神剂的实践本身就可能自然地产生这些隐喻。我主张,产生这些隐喻的致幻实践随着最初的蛇之崇拜一同传播。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们发现危险性较低的致神剂(尤其是在美洲),这种实践可能发生了演化,而蛇的联系则仅在传说中延续。例如,佩奥特仙人掌在仪式中的使用早在距今6千年就已存在。
分析德克萨斯粪化石的论文发表于2019年,并声称这是首次讨论关于仪式性消化毒蛇的考古证据。次年,一篇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分析了在以色列一处洞穴中发现的一批蛇骨,其沉积年代为距今15–12千年。作者并未讨论仪式问题,但确实观察到,有毒蛇类比无毒蛇类更有可能被消化。
这些近东吃蛇者属于纳图夫人,在遗传上与更晚期的埃及人聚为一类。他们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群体,在农业革命到来之前就以自身的革命预示了这一转变。广谱革命(开发更广泛的食物来源,包括鱼类、蛇与兔子等小型动物)被假设为使纳图夫人得以采纳定居生活方式的关键。定居反过来又促成了农业。
考古学家雅克·科万认为,农业的开端并非如此平淡无奇;它标志着人类意识的一次变革。纳图夫人与近东其他人群经历了一场“符号革命”,即一种概念上的转变,使人类能够想象神——那些类似人类、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宇宙中的超自然存在。值得强调的是,对科万而言,这是一种文化而非神经学的变化。
哥贝克力石阵的发掘为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神庙。克劳斯·施密特主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发掘工作,并表示科万的核心观点已被证实:宗教先于农业而出现。25 在 EToC 的解读中,递归思维变得更加自然,与之相伴的是二元性与对未来的思考。农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而蛇之崇拜则是推动因素之一。
要证明距今1.1万年前的毒液致神使用并不容易。然而,在哥贝克力石阵中,有整整 28.4% 的雕刻动物是蛇,是第二常见动物狐狸(14.8%)的两倍。而且,这一统计将成组动物视为一次出现。如果将成群雕刻的蛇按个体计数,那么蛇就占所有可辨识动物的一半。
哥贝克力石阵有时被视为“凭空出现”。但从蛇之崇拜的视角来看,它恰好嵌入一个广为接受的系统发育谱系之中,即蛇被用于死亡与重生仪式。蛇形小雕像是许多靠近哥贝克力石阵的考古遗址中的主导主题,包括早其一千年的 Körtik Tepe。再往北,在西伯利亚的一处墓葬中,一名男孩在距今2.4万年的冰期高峰被埋葬。在他的墓葬中,我们发现了用猛犸象牙雕刻的蛇,其形态酷似眼镜蛇。眼镜蛇(或任何蛇类?)并不生活在如此寒冷的气候中。这些很可能是随人群迁徙而来的外来神祇。显然,它们具有持久的象征力量。(类似地,这一文化还雕刻了许多维纳斯雕像,而此类雕像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广为流行。)
回到维纳斯的母土,人们早在距今1.7万年前就举行无头蛇仪式。在比利牛斯山的一处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两具被斩首的蛇骨骼,而洞壁上则装饰着无头野牛。想象一下,在禁食数日后,借着火光进入那座洞穴会是怎样的体验。对一名入秘者而言,他即将“失去头颅”这一点将再清楚不过。上面的链接指向一位印欧语专家,他将此描述为欧洲最早的屠龙仪式证据。
最后,尽管具象图像最引人注目,但大多数洞穴艺术实际上由抽象符号构成。全球洞穴艺术中存在大约20种左右的符号,被认为是一种原始文字形式,其含义在时间上保持一致。在这些符号中,蛇与鸟是仅有的两种动物形态,其中蛇形符号最早出现在距今3万年前。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中的蛇并非凭空出现,它们属于一种从埃及到中国再到墨西哥都被记忆着的深层且广泛共享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许多学者,如 Buckland、Witzel、d’Huy 和 White,都将美洲与欧亚大陆的蛇神话视为源自同一远古根源。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蛇毒在希腊和印度(以及谨慎地说,在美洲)被用作致神剂(entheogen)。我建议将这些观点结合起来:蛇之所以与创世相关,是因为蛇毒曾作为原始欧亚宗教中的致神剂,而这一宗教传统又传播到了美洲。将蛇毒确立为最初的苏摩(Soma)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若要使之成为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整个世界都必须被纳入这一崇拜之中。
全球范围#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澳大利亚原住民关于“彩虹蛇”(Rainbow Serpent)的岩画。据人类学家 Andreas Lommel 所言,彩虹蛇“通过梦见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灵性祖先——而‘生下了创世’。”
迄今为止讨论的一切,都需要一个大约3万年、以欧亚大陆为根的“系统发育树”(phylogeny)。蛇崇拜可能在欧亚大陆发展起来,并在约1.3万年前随克洛维斯文化传播到美洲。(尽管美洲至少在距今2.3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居住,甚至可能更早,但艺术与复杂石器的最早证据却出现在这一时期。)26 这大致覆盖了世界的大部分区域,但仍然留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澳大利亚这两个棘手地区。它们常被视为文化孤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也有类似的蛇与创世神话。当 Witzel 撰写《神话的起源》(Origins of Mythology)时,他试图为创世神话寻找一个全球性的根源。这使他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处境:如果他将根源设定在约3万年前,他就必须声称澳大利亚与非洲文化的基础是从欧亚大陆输入的。对于以“5万年连续文化”为号召口号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运动者来说,这显然不受欢迎。但世界各地的宇宙起源论(cosmogonies)确实非常相似。那么该怎么办?就像那些将艺术与婚姻追溯到30万年前的人类学家一样,Witzel 的解决方案是提出一个真正古老的非洲根源,在本例中是10万至16万年前27。我认为这站不住脚。十万年对于一个故事的存续来说太长了。我们真的能指望在“传话游戏”式的十万年之后,还能认出一个神话吗?按任何人的标准,这已经进入了进化时间尺度;尚不清楚10万年前的人类是否拥有“灵魂”,更不用说对灵魂的解释。此外,很容易相信澳大利亚人与非洲人,和其他人类一样,在过去3万年中也参与了文化交流。文化是可以传播的!它现在就在传播。我们必须记住,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有些部落拥有创世故事、代词与仪式,而其他部落则没有。对于意识的第一个良好解释,尤其容易传播,因为它并未取代本土的创世神话,而是在填补一个空白。如果这些论点仍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们还可以转向桑人(San)布须曼人的创世神话,它暗示了文化扩散。
南非布须曼人谈到一位造物主 Cagn,他“使万物显现并被造出”(“caused all things to appear, and to be made”)(Orpen 1874, 3)。
“Cagn 给了我们这支舞的歌,并告诉我们要跳这支舞,人们会因此而死,而他会给我们符咒将他们复活。这是一种男女围成圆圈、彼此相随的舞蹈,整夜起舞。有人倒下;有人变得像疯了一样、病了一样;那些符咒较弱的人鼻子会流血,他们会服用符咒药物,其中有烧成粉末的蛇。”——Qing,一位来自德拉肯斯山脉(Drakensberg)的布须曼男子,1873年接受 Joseph Orpen 采访时所述
“恍惚舞”(trance dance)是桑人仪式生活的中心。显然,它是在某个“人”出现、给他们研磨成粉的蛇药,并告诉他们开始跳舞时确立的。涉及蛇的恍惚舞让人联想到遍布美洲的“蛇舞”(Snake Dances)。(霍皮人的蛇舞在脚注28中有所描述。)与美洲一样,桑人的岩画为我们提供了数千年前蛇在宗教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瞥。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Joseph Campbell 的《世界神话历史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of World Mythology)为这幅图配的说明是:“典型罗得西亚楔形风格的岩画,下方为人祭场景,上方为云中女神。灵性使者聚集并攀登一座通天梯,而这座天梯在一道闪电中断裂,闪电则转化为一条雨蛇。南罗得西亚 Marandelles 区。”
Joseph Campbell 将这幅图描述为一个人祭场景(下方),上方则是云中的女神。按照 EToC(注:原文缩写,文中既有)解读,她与宇宙巨蛇(Cosmic Serpent)正在促成死亡与重生。
足够先进的技术与魔法无异。对于最初的“魔法师”而言,这一点更是双重成立。想象一下,将宗教这种“心理—社会技术”引入尚未有宗教(甚至可能尚未有递归思维)的部落。如果最初的萨满带着迷幻剂而来,他们会被记忆为半神29。
当然,“来访教师”并不是文化接触的唯一模式。宗教最初是如何传播的,直指“何为人类”的核心。是否曾有和平的“意识传教士”?最初的萨满部落是否曾以长矛征服世界?抑或这些仪式是通过贸易网络“交易性地”(transactually)被采纳的?以人性而论,很可能三者皆有。然而,Cagn 听起来像是一位传教士,“梦境时光”(Dreamtime)的伟大女神亦然。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澳大利亚岩画,采用“X 光”风格,即描绘人物的骨骼或内脏。此处描绘的“母神”(Mother Goddess)在新时代灵修圈中颇受追捧。某异教网站给出的说明如下:她,与她的姐妹 Djunkgao(有时也包括她们的兄弟)一起,被称为 Djanggawul;生育与繁衍的双重女神;太阳之女;诸母;那些生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人;那些在梦境时光中,从亡者之岛 Bralgu 出发,沿着晨星之路而来的人;那些在抵达“太阳之地”后,朝着落日方向不断前行,从她们永远怀孕的身体中源源不断地产出植物、动物与人类孩童的人;那些为她们的子女提供生活所需与神圣仪式的人;那些无论将她们的 rangga 徽记插在何处,便在何处创造出水泉与树木的人;那些拥有细长生殖器的人。最初,所有宗教生活都掌握在姐妹二人手中,直到被她们的兄弟窃取,他还缩短了她们的生殖器。
澳大利亚有许多创世故事,但一位伟大女神的到来是一个共同主题30。在澳大利亚北部,人们讲述 Djanggawul 姐妹的故事:她们乘独木舟从东方的神话之岛而来。在其他版本中,“我们的母亲”(Our Mother)也是一条吞噬男人的彩虹蛇。她带来了语言、启蒙仪式、艺术与法律。如此深刻的转变理应留下痕迹,因此我们来看看物质证据。
彩虹蛇在整个澳大利亚都受到崇拜,因此很容易认为这必然是一个可追溯到最初人类抵达澳洲时的古老传统。然而,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彩虹蛇仅可追溯到距今6千年前,另有一个可能的1万年前的离群例证。这远晚于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5万至6.5万年前)的证据。鉴于在世界其他地区,人们普遍接受蛇崇拜存在一条“系统发育谱系”,因此彩虹蛇从欧亚大陆传入澳大利亚是合理的推测。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扩散例子。例如澳洲野犬(Dingo)无疑是由人类带入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距今4千至8千年前,但最新证据表明仅在3千年前。因此,这将是与假定的“蛇崇拜浪潮”不同的一波扩散,但它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此外,数种标志性的澳大利亚岩画风格出现在距今6千至9千年前。正如上图所示,这些岩画常以“X 光”风格描绘文明化的灵体。即便是主张澳大利亚宗教已有16万年历史、并由6.5万年前首批登陆者带入的 Witzel,也承认 X 光风格是在全新世从外部传入的。在这些例子之上,Joseph Campbell 还补充了“投矛器、回力镖与盾牌、精细的压力剥片技术、单面与双面尖状器、细石器与石片”。他指出:“毫无疑问,这整套新石器工业是从别处传入的,很可能来自印度。”基于此,Campbell 认为澳大利亚宗教源自欧亚传统31。
最后,还有一股存在争议的基因流入,大约在4千年前自印度传入。显然,在约8千年前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仍为一块陆地时,两地之间也曾发生基因与文化交流。澳大利亚原住民普遍承认彩虹蛇的存在。如果在2万年前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这一传统如今却未延伸至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显得颇为奇怪32。因此,彩虹蛇仅在过去1万年间存在于澳大利亚,并属于欧亚蛇崇拜传统的一部分,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事实上,这正是奥卡姆剃刀所指向的结论。在过去1万年中,还有许多其他文化要素传入澳大利亚;那为何不能包括彩虹蛇?回想一下,Moore 与 Brumm 曾反对“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这一概念,理由是它在澳大利亚仅自距今7千年前才出现。
当然也有其他解释。d’Huy 与 Witzel 都认为,澳大利亚神话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似,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10万年以上的共同根源。但正如我在《反对 d’Huy》(Contra d’Huy)中指出的,这意味着在长达9万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澳大利亚谱系曾崇拜蛇。而在长达6万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萨满教的迹象,更不用说“蛇萨满教”了。最令我困惑的是,这种解释要求我们相信:信息可以在神话中保存10万年,却对过去1万年间 X 光风格艺术、澳洲野犬与更复杂石器技术的引入毫无文化记忆。即便在梦境时光叙事中,已经明确指出艺术、宗教与技术是由乘独木舟从澳大利亚北部以东某岛而来的“人”带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在旁边,乘独木舟即可抵达。放眼澳大利亚之外,艺术、历法与宗教也不过有4万年历史。如果故事真能延续10万年,那么我们理应拥有一些关于“维纳斯雕像”(Venus Statues)的故事——那是被制作了数万年的珍贵宗教物件。我的理论是,我们确实拥有这些故事,它们以夏娃(Eve)、得墨忒耳(Demeter)与 Djanggawul 姐妹的形象存续。除去政治敏感性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要将蛇崇拜追溯到10万年前?若要声称这是一场如此漫长而精确的“传话游戏”,那些“旧石器时代扩散论者”(paleo-diffusionists)就有责任拿出哪怕一丝证据,证明在第一批艺术出现前6万年就存在蛇崇拜。
我希望已经论证了:全球蛇崇拜很可能是一条可追溯至少3万年的连贯传统。与其他研究者相比,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主张。我也认为,蛇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持久力,是因为蛇毒作为致神剂具有实用价值。如果这一点成立,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抗蛇毒药”(antivenoms)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抗蛇毒药(Antivenoms)#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维持者”毗湿奴(Vishnu the preserver)滑行于宇宙之洋之上,安卧在那伽(Nagas)之床上。在这一状态中,毗湿奴以梦将宇宙显化为现实。从他的肚脐中生出一朵莲花,诞生了造物主梵天(Brahma),由他创造世界。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研究中,一位印度男子前往当地的耍蛇人处获取蛇毒“快感”。耍蛇人将蛇牙直接按在他的舌头上给药。我猜想,我们的祖先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与蛇搏斗之前大量服用抗蛇毒药。这一点也可能被保存在神话中。事实上,在我的研究中,最早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神话中的蛇经常出现在潜在抗蛇毒药旁边。例如,在原始印欧语(PIE)传统中,在与巨蛇作战前饮下一杯饮料是一个常见主题。因陀罗(Indra)在与巨蛇 Vritra 战斗前饮下苏摩(Soma),而 Vritra 在神话中扮演的角色与北欧神话中的耶梦加得(Jörmungandr)、希腊神话中的堤丰(Typhon)以及斯拉夫神话中的 Veles 相同。
在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中,一条蛇诱惑夏娃吃下一颗苹果,而苹果是芦丁(rutin)的丰富来源,而芦丁是一种功能性抗蛇毒药。诚然,《圣经》本身并未提到“苹果”。然而,希腊人却在多个场合提到苹果。在下到冥界与蛇尾的刻耳柏洛斯(Cerberus)搏斗之前,赫拉克勒斯(Herakles)必须从赫拉(Hera)的花园中取回一颗赐予不死之身的苹果,该花园由一条龙守护。此外,他还通过接受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为冥界之行做准备,这一秘仪在诸多方面都在庆祝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死亡与重生。狄俄尼索斯被泰坦所诱杀,泰坦向他展示了一条蛇、一面镜子、一种“牛吼器”(bullroarer,一种我们稍后会再提到的神圣乐器)以及一颗苹果。他常被描绘为手持茴香权杖,而茴香同样是芦丁的良好来源,他的圣饮——葡萄酒——亦然。
芦丁也存在于莲花中,而莲花在埃及是创世的象征,并被上图那位安卧在那伽之床上的毗湿奴所持。萨古鲁(Sadhguru)在为那伽神庙(Naga temple)举行圣化仪式时,以姜黄水洗涤蛇像,而姜黄是一种抗蛇毒药(1、2、3、4)。佛陀所坐之树,被一条那伽盘绕,同样是一种抗蛇毒药(1、2、3)。
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后最早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记录蛇的抗毒药。在阿卡德与埃及,两地的抗蛇毒药都是啤酒混合各种草药。在哥贝克力石阵,人们发现了超过一万块研磨石,以及用于酿造啤酒的单粒小麦(Einkorn wheat)。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单粒小麦啤酒为何在抗蛇毒方面尤其有效。在哥贝克力石阵,还发现了可容纳多达200升液体的容器。
《史密森尼》杂志讲述了一个与厄琉息斯秘仪、苏摩与萨古鲁颇为相似的故事。一位在刚果的爬虫学家被蛇喷了毒液。情急之下,他求助于传统医术,找到一位哺乳期母亲,用她的乳汁为他冲洗眼睛。据报道,这一做法确实有效。
在关于死亡、重生与意识的神话中,蛇常常出现在功能性抗蛇毒药旁边。如果蛇毒被仪式化为致神剂,这就非常合理。第一种宗教的目标并不会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亡”。
词源插曲(Etymological Interlude)#
词语联想与神话一样,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一些语言学家认为,甚至有可能重建最初的人类语言。Bengtson 与 Ruhlen 已经提出了数十个全球同源词。据此,原始智人语(Proto-Sapiens)中“思考”的词是 mena,在现代语言中以 man(“思考者”之意)、Minerva(智慧女神)或 mantra 等形式存续;在其他语言中则表现为巴斯克语中表示“大脑”的 munak,马林克语(Malinke)中表示“理解”的 mèn,以及在米沃克湖(Lake Miwok)印第安人中仍保留为“思考”之意的 mena。现代文化浸润在“母语”(Mother Tongue)之中、最初人类的词语仍从我们口中流淌而出,这一想法颇具浪漫色彩。在我看来,这类研究与比较神话学有同样的问题:凡是“全球性的”,就被假定为10万年以上。如果时间线如此之长,那么这些相似性必然是巧合。一个同源词存续的时间不可能那么久,而且我们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10万年前的人类在“思考”。
本节的目标更为有限:蛇相关词汇的词源可以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前,人们将哪些概念与蛇联系在一起。先从 dragon(龙)一词说起,它源自原始印欧语 *derk-,意为“看见”。类似地,诱惑夏娃的蛇——路西法(Lucifer)——字面意思是“光之携带者”(bringer of light)。对于“魔鬼”而言,这是个奇怪的名字,不是吗?
Zmeya 是俄语中表示“蛇”的阴性名词,它源自原始印欧语 *dʰéǵʰōm,意为“土地”或“人类”。拉丁语中的 Homo——如 Homo Sapiens(智人)——具有相同词根。有趣的是,“亚当”(Adam)在希伯来语中也有平行的词源,既可指“土地”,也可指“人类”,字面意思是“(由土地形成的那一位)”。如果蛇参与了这一过程,那么也许同样的词源也附着在它们身上。
“夏娃”(Eve)一名来自希伯来语 Chawwah,其词源为 chawah“呼吸”或 chayah“活着”。不足为奇的是,它也与“蛇”存在联系——“蛇”在阿拉米语中为 hivei。引述希伯来语专家 Robert Alter 的话:
“有人提出,夏娃的名字隐藏着完全不同的起源,因为它听起来与阿拉米语中‘蛇’一词极为相似。她是否是因为与那位狡猾对话者的‘接触性毗邻’而被赋予此名?或者,恰恰相反,在这个名字背后,是否潜藏着对蛇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将其视为与生命起源相关的生物?”——_《摩西五书》(The Five Books of Moses),2004 年,创世纪 3:20 注释
如需更多深度与另一种视角,可参见 Wendy Golding 的硕士论文33。
闪米特语词根 nhš 同时表示“蛇”与“占卜”,并特别指涉“奠祭”(libation)——即献给神祇的饮品34。回想一下:“在《奠酒人》(Libation Bearers)中,埃斯库罗斯(Aeschylus)记载,Drakaina 在被蛇/龙咬伤胸部后,调制并施用了一种由血与乳构成的混合物。”古典学者 Hillman 认为,这一描写正是埃斯库罗斯因“亵渎秘仪”而受审的原因。在希腊与希伯来传统中,蛇都与奠祭相关联。这表明,在远古时代,蛇毒曾是一种神圣饮品。
其他蛇相关研究#
“不幸的是,蛇崇拜多年前就落入了好事之徒之手,他们将其与神秘哲学、德鲁伊秘仪以及那种被称为‘方舟象征主义’(Arkite Symbolism)的骇人胡说混为一谈,以至于如今严肃的学者一听到‘蛇崇拜’(ophiolatry)这个词就不寒而栗。然而,它本身却是一个理性且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神话与宗教中的广泛分布。”——Edward B. Tylor,1871 年
自人类学创立之初,人们就认识到,蛇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被用来代表二元性、主观性与人类的创造。早在 1888 年,C. Staniland Wake 就观察到,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斯基泰人、Zohak、阿比西尼亚人(Abyssians)与中国人都声称自己源自“第一母亲”与一条蛇(常与太阳相关)的结合。一个世纪后,人类学家仍在敲打同一面鼓(只是换了更新的术语)。论文《蛇之子女:阿拉瓦克与特罗布里恩神话中的文化生成符号学》(The serpent’s children: semiotics of cultural genesis in Arawak and Trobriand myth)以讨论埃及人、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如何将自己视为“蛇之子女”为起点,随后在亚马孙(阿拉瓦克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人)中探讨这一主题。
许多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按销量计算,最成功的当属人类学家 Jeremy Narby。他曾与亚马孙的一支部落共同生活,研究萨满教。当地萨满说,他们从“伟大之蛇”那里获得了死藤水(ayahuasca)的配方。在一次死藤水体验中,Narby 遇见了“宇宙巨蛇”(cosmic serpent)。随后,他阅读了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并得出结论:宇宙巨蛇是真实存在的,它将植物的分子知识赐予了萨满。他认为,DNA 看起来像一条双螺旋之蛇绝非巧合,这一观点也启发了他那本书的封面: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为什么蛇在迷幻旅行中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梦中?在创世神话中?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像巨大的 DNA 链?
这本书在亚马逊上的评分是 4.7,有 2200 条评论。“蛇是真的”已经是一个活跃的产业,书名包括:
Proving the Temptation and Fall of Man by the Instrumentality of a Serpent Tempter
Aliens in ancient Egypt : the Brotherhood of the Serpent and the secrets of the Nile civilization
The Serpent Grail: The Truth Behind the Holy Grail, the Philosopher’s Stone and the Elixir of Life
在更为稳健的比较神话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是,蛇的神话并非基于某个特定事物,但它们确实构成了一棵系统发育树。如前所述,Witzel 提出非洲和澳大利亚以外的蛇故事大约有 4 万年的历史。对于宇宙起源论的全球根源,他提出 10–16 万年前,并以非洲桑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中的蛇萨满教为证据,认为这一根源早于“走出非洲”迁徙。同样,d’Huy 提出蛇神话的全球根源为 10 万年前。《创世纪》既是蛇神话,也是宇宙起源论;Witzel 和 d’Huy 声称其中保留了 10 万年以上前故事的显著元素。这些时间线和“蛇是远古外星人”一样奇幻。理性主义者 Tyler Cowen 给外星接触的概率估计约为 10%;你会给《创世纪》有 10 万年历史多少概率?
一个神话若要延续数千年,必然要有社会或心理上的“钩子”。最常见的“沙发派”解释是,蛇是生命与重生的隐喻,因为它们蜕皮。接下来往往会说,它们与冥界相关,因为它们贴地爬行,靠近地面。我敢打赌,这种隐喻在英语课上行得通,但在头骨崇拜中就不行了(例如哥贝克力石阵,第一个蛇神庙)。此外,致神剂的使用使这种解释失效。裸盖菇素蘑菇同样靠近地面,但它们与灵界相关,是因为五克就能把你送往另一个维度。
蛇一直是荣格式心理学家的宠儿,他们并不一定要寻找心理“钩子”存在的原因。对他们而言,神话记录本身就是人类心灵中存在一个将蛇与意识相连的模块的充分证据。生物学家则不太容易接受这一点,提出了若干版本的蛇探测假说。该假说认为,蛇在数千年间是我们的主要捕食者,因此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位置。就像你会在云中看到人脸一样,你会在故事中看到蛇(因此倾向于重复龙的故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蛇神话很多,但并未触及它们的角色。蛇并不主要负责施加死亡。伊甸园中的那条蛇“杀死”了夏娃,但只是像你的母亲那样,在你出生那天就判了你死刑。蛇关乎创造;毁灭只是附带的。此外,为什么蛇在更原始的宗教中更常见?十字架上的基督象征着一条蛇。但你完全可能作为一个基督徒度过一生而从未知道这一点。如果蛇的象征被硬接线进我们的脑中,为什么现代宗教如此少用它?而且为什么恐怖片不是被蛇所主宰?捕食关系无法解释蛇在象征功能上的一致性。
也有一些工作与我自己的观点接近。Hillman 发表了多篇论文,认为希腊人使用蛇毒作为致神剂,但据我所知,他并未将这一视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原始印欧语)。Sadhguru 也将蛇毒描述为致神剂,但他对蛇普遍性的解释最接近 Jeremy Narby。他说蛇理解宇宙的奥秘;那伽(Nagas)以灵体存在,并被各文化的萨满独立接触。语言学家 Daniele Cocice 在博客中写道,与蛇的一场战斗可能产生了原始印欧语中的“我在”(“I am”)。35
也许最接近的是人类学家 Chris Knight 的工作,他认为,蛇神话的全球系统发育树是对女性首次创造文化的记忆。他指出,那将是主体性开端的时刻。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他的兴趣。相反,他写的书旨在表明,文化是由女性联合起来拒绝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而发明的,从而证明共产主义革命是可行的。我不是在编故事!36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主题能让如此多意识形态立场迥异的人达成共识。几个世纪以来,诗人、阴谋论者、德鲁伊复兴者、雅利安爱好者、基督教护教学者以及各种流派的人类学家都说,蛇象征的文化意义与意识有关。数千年来,各种宗教人士——犹太人、万物有灵论者、多神教徒和食人者——也都这么说。蛇是我们呼吸的象征性空气的一部分,因此很难从化学的角度思考它们最初的意义。要跳出这个刻板印象,想象一个世界会有所帮助:在那个世界里,伊甸园中的蛇更明显地是一种致神剂。
心灵航行者 Terrence McKenna 探索的平行宇宙小插曲#
想象一下,如果在世界各地,蘑菇都被认为是人类处境的始祖。羽毛真菌羽蛇神(Quetzalcoatl, the Feathered Fungus)为第一对男女注入了灵魂。因陀罗用一根香菇杖搅动乳海,获得不死甘露。菌丝之母(Mother Mycelia)向夏娃献上自我认知。澳大利亚最神圣的仪式由宇宙松露(Cosmic Truffle)确立,其孢子化为昴宿星团。第一批希腊诗人因揭露裸盖菇素是他们首选的致神剂而触犯了古老的神秘教团。金字塔文献描绘了空间与时间从永恒菌盖(Eternal Cap)中发出,它是灵魂的束缚者。在半打语言中,“fungus”的词源是“人”、“生命”或“圣礼”。在每一块大陆上,岩画都包含如下变体:
这件作品是在 MidJourney v6.0 的帮助下,从一座 1.1 万年前的巴西洞穴中“发掘”出来的。好好珍惜它,因为藐视物理定律是危险的事。许多男人在 3 万年前的高加索深处为捕捉这幅图像而丧命:
最后一幅来自 6000 年前的安达曼群岛:
如果还不清楚,这些都是由 AI 生成的。在那个想象的时间线中,说迷幻蘑菇被用于“萨满教 1.0”并不突兀。**我想要“梗”进文化结构中的主张是:我们就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只不过致幻剂是蛇。它们的毒液作为致神剂起作用,被用作致神剂,而且每一种文化中最古老的故事都将蛇与意识相连。**它也是为数不多的、会主动来找你的致神剂之一。第一剂并不会是自愿的;蛇会以蘑菇不会的方式把问题摆在你面前。
在介绍厄琉息斯秘仪时,我引用了品达暗示终点如同起点:“有福的是那在目睹此事后,踏上地下之路的人:他知道生命的终点以及宙斯所赐的起点!” 古典学家 Károly Kerényi 补充说,“‘终点’与‘起点’看似无色的词语。但它们让入会者想起一个将二者合一的幻象。” EToC 认为这在字面上是真的。秘仪保存了来自旧石器时代的迷幻蛇毒仪式,那时人类心灵仍在形成之中。这些仪式并非文化的偶然部分。那些能够学习“慧性”(sapience)的人实现了他们的潜能,并且除其他之外,生育了更多的孩子。它改变了适应度景观。在厄琉息斯,你可以以与亚当体验自我诞生相同的方式体验自我之死。
迄今为止,我一直使用 3 万年这个数字,因为那是蛇神话最古老的证据。萨满教和“七姐妹”大约从那时起首次出现,支持这一时间框架。或者,也许故事要古老得多,只是证据已经被毁。无论如何,过去大约 4 万年通常被视为人类自我驯化的时期。换言之,一个 3 万年的神话存在于进化时间尺度上。当这些故事首次被讲述时,人类心理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大脑发生了重新布线,蛇毒几乎是帮助处在门槛上的人充分实现其认知能力的完美药物。它赋予一次致神体验,然后为生长新的连接做好铺垫。此外,蛇会主动找到我们,因此它们的毒液被用作早期致神剂是有道理的。第一位夏娃可能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EToC 假定,自我驯化主要关乎二元性、内在符号领域的发现以及递归符号“我”的构建。许多论点取决于伊甸园(或澳大利亚或伊比利亚)中是否真的有一条蛇,用神之知识诱惑夏娃。检验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考察故事中其他不太可能的细节。即:夏娃在亚当之前具有自我意识。为什么在这样一部父权文本中会承认这一点?这是否符合进化理论?在近东以外的考古学和宇宙起源论中是否有证据?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Bradshaw 图像叠加在袋鼠和蛇之上。澳大利亚金伯利地区摄政王河区域。由 Joseph Bradshaw 于 1891 年 4 月绘制
总而言之,将蛇毒视为原初苏摩(Soma)的证据如下:
世界各地的社会都将蛇与人类的创造和文化的开端联系在一起。
蛇毒的急性效应被描述得与其他致神剂类似:戒除成瘾、身心分离以及自我之死。它目前在印度被用作致神剂。有文学和间接证据表明它曾用于厄琉息斯秘仪。
毒液中含有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可能有助于重新布线大脑。
考古证据显示,数千年前在得克萨斯,人们曾以仪式方式食用毒蛇。
各种比较神话学家接受一条长达 3 万年的蛇神话系统发育树,这一时间接近行为现代性的开端。
原初母系社会#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夏娃受蛇诱惑》,威廉·布莱克(1757–1827)
“在安息日之后,索菲亚派遣她的女儿佐伊(Zoe),也被称为夏娃,作为导师去唤醒亚当——他体内没有灵魂——以便他所生之人可以成为光之器皿。当夏娃看到她的男性伴侣被击倒在地时,她怜悯他,对他说:‘亚当,活过来!在大地上站起来!’她的话立刻成为既成事实。因为当亚当站起来时,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她时,说道:‘你将被称为众生之母,因为是你赐予了我生命。’” 《世界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纳格·哈玛第文库中的一部诺斯替派文本,写于公元 3 世纪。
《创世纪》是由一个渴望回到母亲子宫的男人写的。女人、蛇以及任何其他曾赋予意识的事物都被列入他的黑名单。上面引用的诺斯替派作者更接近真相,他认识到夏娃在扶起亚当时所表达的纯粹之爱。纳格·哈玛第文库是一批科普特基督教文本,写于公元 2–4 世纪,但直到 1945 年才被发现。关于索菲亚的这段文字保存(或至少回响)了埃及在古王国(公元前 2500 年)之前的传统,在那里,大母神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实体。37 与蛇引发第一个“我在”一样,人们可以在不诉诸宗教文本的情况下论证:女人在男人之前具有自我意识。
所有人类都依赖他人生存,但女性尤甚。想想怀孕和哺乳期。她在能力减弱的时期需要获得更多食物。群体会帮助她,而这些关系必须通过言语和社会技巧来维系。这对语言和社会智力施加了进化压力。女性大脑在社会生态位中磨砺锋芒,而记忆生态位(memetic niche)正是从中生长出来的。
社会技巧不仅在怀孕期间才需要。平均男性比精英女性运动员更强壮。两性之间在体力上没有可比性,然而这个物种的雌性并不比雄性更不致命。只是她的方法更为微妙。AI 能捕捉到这一点。下面是用“gossip”(八卦、闲话)这个提示词生成的 AI 图像。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使用提示词“gossip”生成的图像。我能说点什么而不被所有人骂吗?
在机器学习领域,这很有争议,因为模型可以被训练去忽略此类模式38。然而,在生物人类学中,八卦并不是坏事。正是它让我们成为人类。你可能因为 Robin Dunbar 的观点而认识他:我们进化到可以在脑中维持大约 150 个社会关系。更广泛地说,他是“社会大脑假说”的倡导者——即人类的一般智力源自社会性思维。在《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梳理、八卦与语言的进化》)一书中,他讨论了处在这一进化过程前沿的人群:
“如果女性构成了这些早期群体的核心,而语言是为了凝聚这些群体而进化出来的,那么自然可以推断,早期人类女性是最先开口说话的。这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语言最初被用来在盟友之间创造情感上的团结感……这与现代人类中女性在言语技能方面通常优于男性,以及在社会领域更为老练这一事实是一致的。”
—— Dunbar, 1996.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第 149 页。
三年前,在《Food of the Gods》(《诸神的食物》)中,McKenna 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
“在古老的狩猎-采集方程式中,女性——采集者——比她们的男性对应者承受着更大的发展语言的压力……语言很可能作为一种主要由女性掌握的神秘力量出现——这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清醒时间待在一起,而且通常在交谈——在所有社会中,她们都被视为群体导向的,与之相对的是被浪漫化的孤独男性形象,即灵长类群体中的首领雄性。”
在一篇最近为《Quillette》撰写的文章中,进化心理学家 David C. Geary 解释了这些差异的神经基础:
在控制大脑体积的前提下,女性相对于男性在语言、社会认知(有时称为情绪智力)、情绪加工与反应性、情境与空间记忆等方面拥有不成比例更大的脑区。
……
语言系统与支持社会信息加工的脑区整合在一起。这些区域包括若干支持面孔识别、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达的情绪加工,以及对目光方向和声音位置(如话语)的敏感性的区域。其中许多区域还与默认模式网络整合在一起,该网络提供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预测模型”。该网络有助于产生能动感、自我意识、个人记忆、以自我指涉方式思考世界(另见此处),以及“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即在心理和情感上将自己置于他人处境之中)的能力。
这些认知差异是基因的结果。最自然的考察对象是决定性别的 X 和 Y 染色体。它们是否对大脑有不成比例的影响?
影响大脑的基因基本上在各条染色体上随机分布。因此,越长的染色体拥有越多基因,因此对大脑的影响越大。很简单。唯一的例外是 X 染色体,它对大脑结构的影响约为预期值的三倍。这一事实产生了如下戏剧性的图表: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X-chromosome influences on neuroanatomical variation in humans | Nature Neuroscience。Heritability(遗传率)指的是一条染色体对神经解剖结构的影响程度。
这说的是大脑的_解剖结构_。那_功能_呢?另一篇论文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困惑:尽管 X 和 Y 染色体几乎没有共享基因,而且对整体脑容量有相反的影响,但它们对与社会加工相关的网络却有相似的影响:
“性染色体剂量的趋同效应优先影响社会感知、交流和决策的中心。因此,尽管几乎完全缺乏序列同源性[同时出现在 X 和 Y 染色体上的基因],并且对整体脑容量具有相反的影响[Y 产生更大的大脑],X 和 Y 染色体对参与适应性社会功能的皮层系统的相对大小施加了趋同效应。”
他们还指出:“X 和 Y 染色体效应在与社会交流和社会情绪加工相关的影像学研究中显著富集。” 性染色体影响的正是实现“我在”所必需的那些区域,并可能在这一能力出现时产生性别差异。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家 Tim Crow 数十年来一直提出理论,认为性染色体对精神分裂症的进化至关重要。在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物种起源的“宇宙大爆炸”模型,其中精神病、语言和大脑侧化的交织发展由性染色体编码。39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语言出现时,人们会预期在性染色体上看到选择信号。事实上,在过去 5 万年间,X 染色体上发生了“非同寻常的”选择。一篇论文分析了受到选择的基因的功能。在顶级候选基因中,他们发现了_“神经相关过程的整体富集”_。在脚注40中,我探讨了 TENM1 的功能——这是 X 染色体上选择信号最强的基因。它对大脑可塑性以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的产生至关重要,而后者是大脑版本的神经生长因子,后者存在于蛇毒中。TENM1 在对大脑奖赏系统至关重要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中表达,并与蛇毒发生相互作用(1,2)。当然,寻找大脑储存意识的部位以及编码这一点的基因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而且这种表述本身就有些愚蠢,许多基因和脑区以复杂方式参与其中。)但我提及这一点,是为了指出未来研究存在富有成果的方向。同样,在这一思路下,我此前写过关于4–25 千年前 Y 染色体上可能存在非同寻常选择的文章。
性染色体大约只占整个基因组的 5% 但却贡献了 20% 的神经解剖学效应量。这仍然低估了它们的影响,因为性染色体还会改变其他染色体上基因的表达方式。睾酮和雌激素水平则像调节许多生物过程的旋钮。举例而言,神经质水平和尾状核体积尤其受到性别特异性基因(即在不同性别中具有不同效应的基因)的显著影响。尾状核是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网络的一部分,而神经质与自我感知相关。
因此,从理论和经验上都有理由相信,总体而言,女性会比男性更早出现递归思维。至少早到足以在文化中被识别出来,并被编码进诸如“女祭司”这样的角色,以及神话中那种原初母系社会或“大女神”的意象。(或许就像“高个子”在文化中被编码为男性一样。)有趣的是,人类学创立之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女性是否发明了文化(而文化需要递归能力)。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在 1861 年出版了《母权论》(The Mother Right),比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早了十年。巴霍芬提出,文化的起源扎根于母子关系之中,主张女性在这些早期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对人类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那是远在碳测年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史前究竟可以追溯多远。圣经式的五千或一万年时间线看起来颇为可信,而理解这一时期的一种流行方法就是从神话中汲取材料。(某种意义上,我在不自觉间又回到了这种方法。)
巴霍芬写作时,纳格·哈马迪文库尚未出土,因此他并未发现像“夏娃向亚当注入灵魂”这样直白的文本。取而代之的是,他从埃及、希腊、克里特、印度和波斯一再举例。雅典命名的故事就是典型证据。城邦曾投票决定是以雅典娜(Athena)还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命名。雅典娜获胜,激怒了尼普顿。引述瓦罗的话:
“为了安抚尼普顿,男人们对女人施加了三重惩罚:女人失去了投票权;孩子不再随母姓;女人失去了被称为雅典人的特权。”
巴霍芬将此解读为证据,表明在某个时期,女性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包括投票权以及将自己的姓氏传给子女的权利。再看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从开天辟地以来对人类的历史叙述。黄金时代相当于伊甸园中尚未具备递归思维的生命,与自然合一地生活。随后是白银时代,农业被引入。赫西俄德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孩子在他慈爱的母亲身边被抚养一百年,是个十足的傻瓜,在自己家中幼稚地玩耍。”
在这些故事中,巴霍芬听到了母系社会的回声。令人惊讶的是,当欧洲人类学家开始从世界各地采集神话时,这一主题被证明具有全球性,而且往往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被讲述。在澳大利亚,有些神秘教团被说成是创立于“梦境时代”(Dreamtime)。如今男人占据主导,但他们这样解释:
“但其实我们一直在偷属于她们(女人)的东西,因为这几乎全是女人的事;既然与她们有关,那就属于她们。男人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做的,除了交配,这些都属于女人。那些属于那些 Wauwelak 的一切,婴儿、血、呼喊、她们的舞蹈,这一切都与女人有关;但每一次我们都得欺骗她们。女人看不到男人在做什么,尽管那其实是她们自己的事,但我们能看到她们那一面。这是因为所有的梦境事务都来自女人——一切……一开始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男人一直什么都没做;我们从女人那里夺走了这些东西。”(Berndt 1951: 55)。Kunapipi: a study of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religious cult
你根本不需要“读懂弦外之音”就能看到一个原初母系社会。而关于这样一次政变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全球性模式。Berezkin 数据库收录了来自多种文化的 37,500 个神话,并细致地按每个神话中出现的主题进行整理。主题 F38出现在横跨南美洲、大洋洲、澳大利亚、亚洲和非洲的 85 个文化中。其内容为:女人曾是神圣知识、圣所或仪式物品的持有者,而这些如今对她们而言已成禁忌。 Berezkin 利用这一主题及相关主题,将新大陆不同文化超级群体与其遗传结构进行关联。引自该论文:
“另一组主题包括若干围绕 F38 展开的母题。女人失去其崇高地位:在最初时代或过去某一时期,女人在社会和/或仪式上的地位高于男人;女人扮演着人与灵之间中介的角色……
这一母题簇还包括:_最初祖先中的男人杀死违反社会规范的女人(F41);在最初祖先的群体中,女人杀死、试图杀死或变形男人(F43A);以及_男人剥夺女人在祖先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F39)。
深入一些例子,亚马孙地区的欣古人(Xingu)讲述了一个女人统治的时代。在当今时代的开端,男人们联合起来,推翻并强暴了她们,夺走了她们的秘密41。在更南边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情况也类似,只是最后只有年轻女孩幸存下来,被当作妻子42。如果想要一个更“可入口”的版本,可以看看电影 《北欧人》(The Northman)43。酋长的儿子被教导奥丁的智慧从何而来:“告诉我,奥丁是如何失去他的眼睛的?为了学习女人的秘密魔法。永远不要去探求女人的秘密,但要始终倾听她们。正是女人知晓男人的奥秘。”
若想了解更多,你可以观看电影中的启蒙仪式场景,或查阅上文脚注。但没有人会否认,关于原初母系社会的神话是一个全球现象。争论在于如何分析。反对将这些故事视为“真相内核”的主要论点是:当下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母系社会。因此,关于这些神话的主流解释是,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宪章,用来为女性的被压制地位提供正当性:“在混乱时代是女人统治,而当男人接管后,情况才变好。” 这在我看来并不合理。为被压迫者编造一个光辉的起源故事,并不是维持统治的有效策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奴隶制度是通过一个关于“失落的黑人统治(Afrocracy)”的神话来加以辩护:在从前的混乱时代,像哥伦布和耶稣这样的人都是黑人,而我们已经看到那导致了什么。为了避免这样的混乱,他们的后代现在可以被买卖。 若真有这样的叙事出现,那会令人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如果罗马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和科曼奇人也都对他们的奴隶讲述类似的变体。此外,还有其他被压迫阶层,比如儿童或“不可接触者”。为什么唯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会通过关于她们曾经拥有权力的神话来加以正当化?在人类学中,这一标准解释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就这么回事”的故事(just-so story)。
到了 2024 年,多数相信曾经存在原初母系社会的人,对达尔文式进化论持怀疑态度。他们希望传达一种政治信息:父权制是可以选择的,而“强权即公理”并不成立。然而,一旦你接受神话可以在进化时间尺度上延续,我们的母系起源就变得可信,甚至是可以预期的。女性很可能是意识的先锋。如果她们往往比男性更早达到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那么她们在政治和宗教上就会比男性拥有更多权力。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母系社会。男人在猎杀猛犸象,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也相当能干。这里的主张是:文化——我们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主要是女性的发明。
表面上看,“以原初母系社会作为父权制的社会宪章”是一个极其奇怪却又反复出现的策略。但更重要的是,神话中还有一些细节,是这一解释无法说明的。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有神圣仪式被说成是从女人那里偷来的故事。这些神圣仪式使用同一种器物:牛吼器(bullroarer)。
牛吼器:传播论者的图腾#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牛吼器系在一根绳子上旋转,会发出嗡嗡声,常被说成是上帝的声音。这一件是用猛犸象牙制成,来自欧洲马格德林文化时期。
“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传播最广、最神圣的宗教象征。” ——阿尔弗雷德·C·哈登(Alfred C. Haddon),1898 年
狄俄尼索斯(Dionysus)和宙斯的许多子女一样,并非出自其妻赫拉(Hera)。赫拉心生嫉妒,唆使年长的神祇——泰坦(Titans)——在他还是孩童时将其杀害。他们用各种器物引诱他——一面镜子、一只苹果、一条蛇、一个陀螺和一只牛吼器——然后将他肢解。但如同许多神祇一样,他又复活了。得墨忒耳(Demeter)(有时是瑞亚 Rhea 或雅典娜 Athena)找到他,将他散落的肢体重新拼合。这一循环在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中被反复上演。
如前所述,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有将昴宿星团(Pleiades)视为“七姐妹”的神话,包括希腊和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七姐妹”歌线(songline)与女性启蒙仪式密切相关,而这些仪式被说成是后来被男人偷走的。与厄琉息斯一样,牛吼器也在其中被使用。这是一组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从统计学角度,我们可以确信,两个地方的“七姐妹”故事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根源。同样,两种文化都有揭示世界如何被创造的“秘仪”,并使用相同的物质器具。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些秘仪与“七姐妹”一样,拥有共同的文化根源。
在澳大利亚,女性如今被禁止参与这一挥舞牛吼器的教团。这相当典型。罗伯特·H·洛维(Robert H. Lowie)早在 1920 年就写道
44:
“问题不在于牛吼器究竟是被发明了一次还是十几次,甚至也不在于这种简单玩具究竟是一次还是多次被纳入仪式关联。我自己就曾在极其庄严的场合看到霍皮族(Hopi)笛子兄弟会的祭司挥舞牛吼器,但我从未想到要把它与澳大利亚或非洲的神秘仪式联系起来,因为那里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人必须被排除在这一器物的视野之外。症结正在于此。为什么巴西人和中澳大利亚人会认为女人看到牛吼器就得处死? 为什么在西非、东非和大洋洲,人们如此一丝不苟地坚持要让女人对这一器物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有什么心理学原理会驱使埃科伊人(Ekoi)和博罗罗人(Bororo)去禁止女人了解牛吼器,在这样的原理被提出之前,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从一个共同中心扩散的假设作为更可能的解释。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和非洲男性部落社团入会仪式之间存在历史联系。” ——罗伯特·H·洛维,《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第 313 页
你完全可以怀疑这是不是被断章取义,或者洛维是不是某种怪人。事实并非如此。他曾两度担任旗舰期刊《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主编45,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的类似论述。事实是,牛吼器在世界各地都被视为神圣之物,而且女人往往被禁止观看。EToC(Entheogenic Theory of Consciousness,致神论意识假说)的解释是:女人发明了仪式,包括男性启蒙仪式,而最早传播开来的形式使用了牛吼器。让女人参与男性启蒙的一个失败模式,就是男人以暴力方式将她们逐出“男孩俱乐部”,而这在许多地方都曾上演。
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学家本应已经解答牛吼器之谜。然而,这种器物的存在是一个令人不适的事实,因此长期被搁置在冷宫。牛吼器研究权威贝丝·哈根(Bethe Hagen)在 2009 年写道:
牛吼器和蜂鸣器曾经是人类学家耳熟能详、深受喜爱的对象。它们在这一学科内部作为标志性文物,象征着文化相对主义对“独立发明”的坚持,尽管跨越人类历史数万年的证据(大小、形状、意义、用途、符号、仪式)都指向扩散。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直到今天,这些器物仍在不断被(?)发明,并以许多古老的方式被重新赋予象征意义。
注意,哈根并不是传播论者(因此她提出“再发明”的说法)。但她指出,最自然的解释是扩散,只不过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坚持,这一方向从未被认真追究。再看另一位非传播论者托马斯·格雷戈尔(Thomas Gregor),他在 1973 年也有类似论述:
“对‘传播论’人类学的兴趣早已消退,但近期证据却与其预测高度一致。如今我们知道,牛吼器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器物,来自法国(公元前 13,000 年)和乌克兰(公元前 17,000 年)的标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深处。此外,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1971)——如今承认,牛吼器属于最早迁徙至美洲的人类所携带的‘工具包’之一。然而,现代人类学几乎完全忽视了牛吼器广泛分布和古老谱系所蕴含的宏大历史意义。” ——《焦虑的欢愉:一个亚马孙民族的性生活》(Anxious Pleasures: The Sexual Lives of an Amazonian People)
我认为,牛吼器曾是女人发明的原初宗教的一部分,用来帮助入会者获得“我在”这一顿悟。考虑一个在希腊和埃及都出现的奇异故事。得墨忒耳有时被认同为“众神之大母”(Great Mother of the Gods)。她伪装成老妇来到厄琉息斯,国王和王后收留了她,她便成了他们儿子德摩丰(Demophon)的保姆。为了回报他们的款待,她打算赐予德摩丰不死之身。这需要每晚将他放入火中,并以神馐(ambrosia)哺育他。某晚,他的母亲撞见他被火焚烧的情景,便中止了仪式。得墨忒耳于是显露神性,并将厄琉息斯秘仪作为临别赠礼。(记住,这些秘仪是由“‘龙女’,她们负责‘烧尽’人的凡俗性”来主持的。)德摩丰的兄长特里普托勒摩斯(Triptolemus)也学会了秘仪和农业之术。得墨忒耳赐给他一辆由蛇拉动的战车,让他将这些技艺传播到世界各地。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特里普托勒摩斯,蛇崇拜的传教士。
埃及人则讲述了一个与之惊人相似的故事,主角是伊西斯(Isis),她是他们的“大秘仪女神”。伊西斯成为黎巴嫩比布鲁斯(Byblos)王子的保姆,每晚将他放入火中,被王后发现后中止仪式,随后她显露神性。
在人类学中,没有哪个母题像“失落的以色列支派”那样令人反感,但在我看来,认为澳大利亚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是特里普托勒摩斯或得墨忒耳的“失落信徒”,并非不合理。我并不是说希腊人或埃及人曾亲自造访澳大利亚。蛇崇拜的扩散远早于这些文明。例如,在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距今约 11,000 年)就发现了牛吼器。但一旦你承认神话可以延续 1 万或 10 万年,那么特里普托勒摩斯传教工作的某种“真相内核”就变得可信。蛇的神话及其仪式确实曾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这些神话被记住了,那么为什么它们的传播不会被记住?牛吼器是理解蛇神话何时、为何扩散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线索。
澳大利亚的“梦境时代”可以被解读为接受秘仪的过程。“七姐妹”、大母神或彩虹蛇(Rainbow Serpent)带来了文化,通过神圣仪式将内在生命固化下来。(有时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燃烧仪式”。)
如此剧烈的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语言。在《代词的不合理有效性》(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Pronouns)一文中,我探讨了这样一个想法:表示“我”的词可能是随这些仪式一起传播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人称单数在世界许多语系中要么是 ni,要么是 na:澳大利亚语系、巴布亚新几内亚跨语系、巴斯克语、北高加索语系、汉藏语系、科伊桑语系(桑人)、安第斯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韩-日-阿伊努语系、伊特鲁里亚语、科尔多凡语系、吉利亚克语、Almosan 语系、Hokan 语系、奇布查语系_以及_Paezan 语系。注意,这是一份保守的清单。_澳大利亚语系_和_巴布亚新几内亚跨语系_可以进一步拆分为数十个使用 na 的小语系。46
最后,牛吼器甚至可能是仪式顿悟的一个“活性成分”。当被旋转时,它会产生一种频率,桑人(San Bushmen)曾利用这种频率来进入改变意识状态,这一实践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9,500 年。如前所述,他们的恍惚舞蹈是在造物主卡恩(Cagn)来到他们中间,给了他们蛇粉,并让他们开始跳舞时确立的。他们会死去,但之后又复活更新。这一序列是世界各地文化的基础。
死亡与重生#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尼哥底母问。“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约翰福音 3:4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告诉我,奥丁是如何失去他的眼睛的?为了学习女人的秘密魔法。永远不要去探求女人的秘密,但要始终倾听她们。正是女人知晓男人的奥秘。”
让“我”的意识沉淀成形,远不止需要蛇毒。必然会有一整套仪式,旨在帮助某人意识到自己并不仅仅是肉身——这是一种必须亲身体验才能理解的领悟。这会涉及死亡与重生。从机制上看,这很合理。人在死亡(或濒死)时会分泌 DMT,而压力情境会让教训更牢固地刻印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文化的基础确实曾扩散开来,神话记录表明,它包含了仪式性的死亡与重生47。
米尔恰·伊利亚德是现代比较宗教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生命的晚期,他写作了关于启蒙仪式的著作。伊利亚德认为,最古老的启蒙形式是对“时间之初”的再现——在那时,神、造物主或文化英雄确立了“向灵性而生”的方式。而这几乎总是以仪式性的死亡为前奏。
启蒙对于理解原始心态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向我们展示:真正的人——精神之人——并非天生具备,也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他是由年长的师傅们“造就”的,依照神圣存在所启示并保存在神话中的范式。 ——《启蒙的仪式与象征:诞生与重生的秘仪》(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The Mysteries of Birth and Rebirth),1984
伊利亚德并不关心生物进化。对他而言,“时间之初”是我们通过参与仪式和文化而成为人的时刻。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作者(以及当今许多人)一样,他认为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在 3–4 万年前于欧亚大陆发展起来,并从那里扩散。在书中,他展示了宗教——尤其是在最原始文化中的宗教——是回溯性的,回望那个将精神生命引入世界的神话时刻。在比较了澳大利亚和南美的启蒙仪式后,伊利亚德解释说,在世界各地,这些仪式都是由:
某些与人类历史上一个可怕却又决定性时刻相关的神话人物引入的。这些存在揭示了某些神圣的奥秘或某些社会行为模式,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并因此改变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尽管是超自然的,在时间之初,这些神话人物过着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人类生活相比较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们经历了紧张、冲突、戏剧性事件、攻击、痛苦,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死亡——通过第一次在地上经历这一切,他们奠定了人类当下的存在方式。启蒙向新入会者揭示这些原初冒险,并在仪式中重新演绎这些超自然存在神话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
我努力引用最优秀的学者——像克雷尼(Kerényi)或伊利亚德这样的人,他们通晓多种语言,沉浸在过去的世界中。我所依凭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权威,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都说,在最初,生命的奥秘是由来访者教给他们的。如果行为现代性——包括创世故事和仪式——已有 4 万年历史,而神话可以延续大约这么久,那么这或许真的是一种记忆。我的“小小贡献”是提出这样一个设想:这一基础是由使用蛇毒作为致神剂(entheogen)的女性发展出来的。我的“宏大贡献”则会是展示这一点如何改变了适应度景观——即创世神话其实是来自认知上“异质时代”的故事,那时女族长们向“人”之中注入了灵魂。
需要澄清的是,我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弱 EToC”版本:递归自我意识在过去 5 万年间是人类自我驯化的驱动力之一,而女性在这一过程中拥有早期优势。在那段“诡异谷”时期,蛇崇拜兴起,提供了关于精神生命的解释,而秘仪随之传播。这些都是值得展开的全新观点。EToC 的最强版本则认为,相关仪式帮助男性“追赶上来”,这一点应当在过去约 1.5 万年中 Y 染色体上留下强烈选择的痕迹。这一版本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值得讨论,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预测。
结论#
[Image: Visual content from original post]夏娃,众生之母。Andrew 使用 Midjourney v6.0
特洛伊城曾一度被认为只是一个神话,直到有个疯子跑去把它挖了出来。我的项目与此类似,但必须被发掘出来的,是那些若没有 EToC(E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夏娃意识理论)就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昴宿星团的“七姐妹”、响板(bullroarer)、原初母系社会以及关于蛇的神话会遍布全世界?为什么这些又如此频繁地与意识的起源相联系?如果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根源已有 10 万年历史,为什么递归思维的证据却只有 5 万年?如果我们在 20 万年前就已经拥有递归思维,为什么我们的物种当时没有就此征服世界?艺术大约出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智人(Homo Sapiens)吸收或击败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nsis)、龙人(Homo Longi)和吕宋人(Homo Luzonensis)——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言。 与此同时,人类的头骨形状正在发生改变,与智力、语言和大脑可塑性相关的基因正在受到选择。
毫无疑问,这里的利害关系远比特洛伊要重大。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作为一种信条,许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在过去 5 万年中人类并未发生显著进化。这导致了一种尴尬的折中:我们在那段时期开始表现得“像人类”,但这些能力必定早已潜伏在我们更久远的过去。人类心灵是一块白板,而 5 万年前的人类不过是发现了粉笔,可以这么说。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适应度景观。文化书写其上的那块板对自然选择的力量不受影响。它如何产生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奥秘,但我们可以确信,在认知上,人类与 20 万年前的穴居祖先是一样的。进化不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尺度上运作。
我承认,这也可能是真的。但让我难受的是,这一模型的支持者在否定关于我们起源的 4 万年传统时是多么轻率。通俗科学作品对宗教与灵魂充满轻蔑。例如,在《递归之心》(The Recursive Mind)中,Corballis 写道:“我们可能拥有某种精神超越性的观念,是由勒内·笛卡尔赋予科学与宗教上的正当性的,他有时被视为现代哲学之父。” 接着他哀叹,竟有整整 90% 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最后,他给宗教读者扔了一根骨头:
“我们也不应对宗教评判过于苛刻,因为有充分理由认为,宗教信仰本身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或许不是直接的,而是作为群体生存选择的结果。我们人类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生物,而宗教提供了一种确保群体凝聚力的机制。宗教确实给进化论带来了问题,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而最终的讽刺也许在于,对宗教的解释本身就根植于进化。”
当然,我会把这个框架倒过来。最终的讽刺也许在于,我们如何进化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圣经》中。如果女性首先具备自我意识,那么《创世记》关于人类起源的叙述就可能在进化时间尺度上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有些故事确实延续了那么久。当故事讲的是一场“特大洪水”时,人们会把它当作一个关于原住民知识如何保存冰河期后海平面上升故事的暖心案例。那么,我们又能从与之同时发生在近东地区的象征革命(Symbolic Revolution)中学到什么?那个地区在五千年前发明了文字;这个故事只需要以口头形式传承一半那么久即可。伊甸园中的蛇与苏美尔的雌龙提亚马特(Tiamat)很可能就是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石柱上那些蛇的化身。48 又或者,看看澳大利亚在过去一万年中向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转变的过程?如果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可以延续一万年,我们同样可以从中了解古代文化,甚至也许是心理层面的变迁。梦境时光(Dreamtime)或许并没有那么久远;它可能仍被记得。
人类进化的困境在于,我们在奇妙的程度上、在类别上都与其他任何动物截然不同,但自然选择却是以渐变方式起作用。为了解决这一点,人们可以缩小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距离(例如 Corballis),或者假定认知上存在一个阶跃式的飞跃(例如 Chomsky)。与其把人类拉下神坛49,或在生物学上玩弄概念,EToC 用一种直接的基因—文化互动来处理这一难题。递归文化得以传播,与之相伴的是对递归自我意识的选择。其强版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原初母系社会、蛇毒作为致神剂、智性悖论(Sapient Paradox)50,以及男性启蒙仪式在全球的扩散——而这些预测得到了广泛数据的支持。而且,即便原初蛇崇拜并未影响进化,它的存在本身仍值得理解。如果在印度、得克萨斯和厄琉息斯,人们都曾为求得启示而服用蛇毒,那么《创世记》所描述的就是一个真正古老的传统。
我之所以掉进这个兔子洞,是因为我在思考为什么《创世记》如此贴切地描述了人与内在声音认同的过程。这似乎是一条通往意识的可行路径,是那种女性会首先发现的东西,而蛇毒可能有所助益。许多研究者声称,关于七姐妹、蛇的神话,或世界各地的宇宙起源论可以追溯到 5 万—10 万年前。行为现代性似乎可以追溯到 7000—4 万年前,视地区而定,因此《创世记》可能是_人属(Homo)_变得具备理性的记忆。由此,EToC 应当被严肃对待。也就是说,它应当被批评、被置于可证伪性检验之下,并接受科学方法的一切严格要求。像往常一样,这是一项集体事业,所以请加入进来。
有位智者曾说过,大多数书本其实应该写成博客文章。然而,对_这_篇文章来说,最合适的形式其实是一本书。我希望有更多篇幅来展示原初母系社会、蛇与响板之间的联系,例如。或者讨论人属在 20 万年前甚至一百万年前就拥有象征性思维的论据。我也希望在 AI 安全的语境下发展这些想法,那更接近我的背景。我们目前只有 n=1 的通用智能出现样本,而我们正要再造一个。这对夏娃和普罗米修斯来说结局如何,你是知道的,对吧?不过,要做这些事,我需要有人来审视这些想法。如果你希望看到更多内容,请分享这篇文章:每当有人问,为什么人类在 20 万到 1 万年前没做多少“大事”;每当“嗑药猿理论”(Stoned Ape Theory)被提起;每当有人好奇,这些该死的蛇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也请留言告诉我,你认为 EToC 中哪些部分可行、哪些不行。读者反馈在从 EToC v2 → v3 的过程中帮了大忙。
在澳大利亚中部的 Urabunna 人中,未入会者被教导相信,那声音是一个灵体的声音,“它会把男孩带走,把他所有的内脏取出,再给他装上一套新的,然后把他切割成一个已经入会的青年。男孩被告知,绝对不能让女人或小孩看到这根木条,否则他和他的母亲以及姐妹都会像石头一样倒地身亡。”再往北,在卡奔塔利亚湾一带的 Anula 人告诉她们的女人,牛吼器的呼啸声是由一个灵体发出的,这个灵体会把男孩吞下去,然后再把他以一个已入会青年的形态吐出来。在生活于新几内亚胡恩湾一带的 Bukaua 人的启蒙仪式中,新手的母亲们被告知,那些叶片状木板发出的轰鸣声,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食人怪物的声音,它会吞下年轻小伙子,然后再把他们吐出来。在所罗门群岛和法属群岛中,牛吼器同样对女性保密,女人们相信那种奇怪的声音代表着一个灵体的声音,而新不列颠的 Sulka 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这个存在偶尔会吞食未入会者。上述例证取自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文献。但当类似的观念出现在非洲各地时,我们又当作何感想?尼日利亚南部的 Ekoi 人不允许任何女人看到牛吼器,或知道它们发声的原因,而在遥远的东非 Nandi 人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 Yoruba 人中,女人确实被允许观看甚至触摸牛吼器,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看到它在运动中。弗罗贝尼乌斯博士一个带有玩笑意味的动作——暗示他要把牛吼器在空中旋转——就足以让在场女性惊恐发作。据说在古代,如果女人在男子社团游行、这些器具在空中挥动时出现,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死。最后还必须举出一个南美的例子。巴西中部的 Bororo 人在其丧葬仪式上会挥动牛吼器,这就是所有女人要跑进树林或躲在家里以免死亡的信号。在这里,男人们也同样相信,仅仅看到牛吼器就会自动导致女人死亡,而冯·登·施泰嫩博士被郑重告诫,绝不可把他买到的标本展示给女人或小孩看,以免造成死亡事故。
这些相似之处绝非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引起了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兴趣,他将其解释为“相似的心智,以简单的手段朝着相似的目标运作”的结果,并明确否认需要假设“共同起源或文化借用,来解释这一广泛分布的神圣物件”。在这一解释上,冯·登·施泰嫩教授追随了他的看法,他指出,如此简单的装置——一块系在绳子上的木板——几乎不能被视为对人类创造力的严峻考验,以至于需要假定在文明史上只有一次发明。但这就误解了问题的实质……
“这两类数据【遗传和语言】也都显示,人口从东北向西南扩张。Bowern 说,这次迁徙发生在过去一万年之内,很可能是以连续的浪潮形式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现有语言被新语言覆盖。这次扩张似乎也与一种名为‘背缘石片’(backed edge blade)的石器创新相对应。但伴随而来的基因流动只是涓涓细流,Willerslev 说,这表明只有少数人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就好像有两个男人走进一个村庄,说服所有人说一种新语言并采用新工具,发生了一点性接触,然后就消失了,’他说。随后,这些新语言继续发展,遵循着旧有人口分化的模式。‘这真的很奇怪,但这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对数据所能做出的最佳解释。’”
宇宙起源神话和启蒙仪式的传播可以解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过程。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和澳大利亚都在男性启蒙中使用牛吼器,并且都说这是很久以前从女人那里偷来的。不仅如此,这两个语系都用“na”来表示第一人称单数。此外,PNG 的语言学家估计,PNG 语系中所有现存语言的基础是在约一万年前从欧亚大陆传入的,并淹没了先前存在的语言(尽管那一层的一部分仍以“古老底层”的形式存留)。在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和 PNG 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扩散过程会在那条并不存在的澳大利亚边界处停止?许多证据线索都表明,它并没有停止。
I know that I hung on a windy tree
nine long nights,
wounded with a spear, dedicated to Odin,
myself to myself,
on that tree of which no man knows from where its roots run.
No bread did they give me nor a drink from a horn,
downwards I peered;
I took up the runes,
screaming I took them,
then I fell back from there.
这是“被悬挂的神”(hanged god)母题,其中包括奥丁、耶稣、普罗米修斯、倒吊人塔罗牌,可能还有 Ixtab。“我献身于我自己”(myself to myself)以及长矛的细节与耶稣的受难——祂向自己、即圣父上帝献祭——如此相似,以至于新约对其影响仍存在争议。关于仪式上的相似性,可参见“hook swinging”(钩悬仪式)。
“人们往往假定,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与其他动物在根本上不同。比如,大多数人会认为,卖掉、烹煮或吃掉一头牛是可以的,但对屠夫做同样的事就不行。这会是,嗯,不人道的。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容忍把黑猩猩和大猩猩关在笼子里展览,却会对把彼此关起来感到不安。同样,我们可以去商店买一只小狗或小猫,却不能买一个婴儿。
对我们和它们而言,规则是不同的。即便是最顽固的动物权利活动家,也是在为动物争取动物权利,而不是人权。没有人提议赋予猿类投票或参选的权利。我们本能地把自己看作处在一个不同的道德与精神层面上。我们也许会埋葬死去的宠物,但不会指望狗的幽灵来纠缠我们,或者在天堂里等着我们。
然而,要为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找到证据却很困难。”
吠也罢,不吠也罢,这是个问题——究竟是心灵更高贵,去忍受命运所赐的松鼠与邮差,还是抬腿对这烦恼之海撒尿,从而终结它们 ↩︎
词汇假说(Lexical Hypothesis)认为,关于人格差异的最完整模型,已经嵌入在我们用来描述彼此的语言之中。进一步说,人格心理学家的任务不是去理论化人格的所有面向,而是要在自然语言中以经验方式识别它们。因此,大五人格是通过分析人格形容词的分布而被识别出来的。在他们最成功的人格模型中,心理学家放弃了理论构建,而是把判断权交给大众。语言这一协作性工程可以勾勒出看似不可理解的抽象之物的形状,包括关于人类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因此使用“灵魂”一词。 ↩︎
我采纳这种偏见,是因为它由“创世神话具有信息性”这一前提所暗示。如果宇宙起源论中的信息可以在进化时间尺度上保存下来,那么进化时间尺度就必须相对较短。考古学家则明确表示,他们采纳相反的偏见。这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当然也可以由对漫长进化时间线的强先验来加以辩护。 ↩︎
从技术上讲,jpeg 是一种有损算法,因此它并未存储完全相同的信息。 ↩︎
许多递归过程共享相同的认知资源。递归音乐阐明了支持旋律层级生成与检测的神经机制:“在语言(Perfors et al. 2010)、音乐(Martins et al. 2017)、视觉(Martins et al. 2014a, b, 2015)以及运动领域(Martins et al. 2019)中,都已证明了使用递归层级嵌套(recursive hierarchical embedding, RHE)的能力。尽管行为研究表明,RHE 在这些领域中是由相似的认知资源实现的(Martins et al. 2017),但尚不清楚它在多大程度上也由相似的神经机制所支持。” ↩︎
你可以在 Aella 对“美好性爱”的定义中听到《奥义书》的回响:“不过在这里,[美好性爱]指的是类似‘在体验中迷失自我’的东西。当我回顾那些我认为很棒的性经验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性本身’,如果这说得通的话?就好像我不再是 Aella 的大脑,在做思考的事情,而是 Aella 的身体,在做高潮的事情。我已经忘了剧情,我不记得剧情是什么,我只是一个性生物,发出一连串不断的声音。”那原初的主题星座:合一,然后是自我,然后是对与他者合一的渴望。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恩奇都被妓女沙姆哈特文明化,这并非偶然。她更应被理解为女祭司;性会重写自我的边界。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被加以利用。 ↩︎
如果某个性状是适应性的,那么其在种群中的频率会根据育种者方程(Breeder’s Equation)在每一代发生变化:其中 Δz 代表每代表型的变化量,h^2 是狭义遗传率(即该性状的加性遗传贡献),β 是选择梯度。在我们的例子中,相关性状的遗传率(h^2)大约为 0.50。为了估计选择梯度(β),我们考虑性状与适应度之间的相关性。在 r = 0.1 的情况下,并假定适应度(如存活子女数)的标准差为 1 以简化计算,选择梯度可近似为:β = r × 适应度标准差 = 0.1 * 1 = 0.1。将这些数值代入育种者方程,每代表型变化量(Δz)为:Δz = 0.50 × 0.1 = 0.05。这意味着该性状每代会改变 0.05 个标准差。为了确定发生一个标准差变化所需的世代数,我们计算:世代数 = 1 / 0.05 = 20。这意味着需要 20 代才能改变一个标准差。考虑到一代通常约为 25 年,这意味着大约需要 500 年(20 代 * 25 年/代)才能改变一个标准差。现在,让我们计算在 2000 年和 5000 年中,该性状在种群中会发生多大程度的偏移:对 2000 年而言:2000 / 500 * 1 个标准差 = 4 个标准差。对 5000 年而言:5000 / 500 * 1 个标准差 = 10 个标准差。这些计算表明,在给定假设下,该性状在 2000 年内可以偏移 4 个标准差,在 5000 年内可以偏移 10 个标准差。 ↩︎
本文的目的在于区分我们的文化与基因根源。然而,即便你假定我们的基因与文化根源是相同的,也没有必要追溯到 30 万年前。考虑另一种模型。最近这篇论文发现了“回流非洲”(Back to Africa)群体的遗传证据:
【图像:原文中的可视化内容】
AA 是古代非洲人,XAFR 是与非洲人混合的“幽灵”种群,ASN 是亚洲人。XAFR 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一起,被建模为在 60 万年以上前就与人类分离。71 千年前,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群体从古代非洲人中分离。58 千年前,一个回流非洲群体从欧亚人中分离,并取代了古代非洲人以及 XAFR。“我们的方法预测,回流非洲的混合比例高达 91%(置信区间 90.28–91.57),这表明古代非洲人群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得通。如果走出非洲群体拥有某种优势,使他们得以吸收/征服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那么这一点在非洲同样适用。需要明确的是,这同样只是另一种模型,不应被视为地面真相(ground truth)。再强调一次,本文的目标是区分我们的模因与基因起源;我们完全可能在最早的分支之后才“成为人类”。但这一模型有助于思考人类最近共同祖先(MRCA)的时间,以及这如何影响相关争论。该模型将 MRCA 定在不超过 5.8 万年前。实际上,它更为近期,因为完整的人类谱系在过去 5 万年更像一团荆棘丛。欧洲与亚洲并非在 3.3 万年间完全基因隔绝;正如模型所示,大陆之间存在大量基因交流。
再来看把理性(sapience)追溯到 20 万年前的其他证据。较早的年代往往依赖母系与父系 MRCA:Y 染色体亚当或线粒体夏娃。这给出了约 20 万年的时间点。但设想一种情形:XAFR、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的 Y 染色体或线粒体 DNA 谱系在现代人中幸存下来。这会突然让我们的物种变成 60 万年历史吗?这会让婚姻、艺术与讲故事等普遍现象也变得有 60 万年历史吗? ↩︎《智人的崛起:现代思维的进化》(The Rise of Homo sapien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Thinking),第 238 页。Carl Ruck 在《致神剂、神话与人类意识》(Entheogens, Myth, and Human Consciousness)中给出了同样的年代:“人类自晚期旧石器时代智人首次出现以来,留下了可追溯约 3.2 万年的认知经验记录。”他甚至猜想,世界各地实施的启蒙仪式可以追溯到我们发现最早艺术的洞穴神庙,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提到:“在今天仍然举行洞穴仪式的原住民中,男女有各自独立的洞穴。洞穴被视为部族从地底原初出现之地、祖先之家,以及重述其最秘密神话的场所。手印被解释为其古老祖先的证据,而新的手印则在血腥的成年礼过程中被描摹。如果说这些遍布世界的绘画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大概就是萨满或启蒙性质的宗教仪式。” ↩︎
关于行为现代性的证据:“我们将论证,澳大利亚的这类证据是零散的,许多标志直到中—晚全新世才出现。澳大利亚更新世的象征性活动证据最接近于欧洲与非洲的早期与中期旧石器时代。”“澳大利亚的考古记录在关于早期象征行为的性质与出现的争论中很少被考虑(但参见 Holdaway & Cosgrove 1997);本文试图纠正这一失衡。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在中—晚全新世时期快速、遍及大陆的文化变迁之前,澳大利亚文化变迁的节奏是缓慢而零星的,象征性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也是零散的。我们认为,澳大利亚更新世与全新世考古记录中的模式,与非洲和欧洲中—晚期旧石器时代考古记录中的模式存在广泛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不能被轻易忽视。将‘短程’现代行为起源论者所倡导的现代人类行为考古特征应用于澳大利亚更新世,意味着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直到相对近期——也许仅在过去 7000 年——才具备行为现代性。如果否定这一结论——正如我们所做的——那么‘短程’模型在逻辑与有效性上都会出现问题。”——《象征革命与澳大利亚考古记录》(Symbolic revolutions and the Australian archaeological record),2005 ↩︎
人类学家的表述在这一点上同样是错误的。把时间定在晚于 30 万年前,并不要求“每个人、在每个地方,恰巧在 6.5 万年前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时间突然变得完全人类”。在 6.5 万年前并没有“完全人类行为”的证据,当它在 4—5 万年前出现时,也并非均匀分布。考古学表明,那是一个历时数万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
终止时间点很难确定。他工作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递归的进化需要许多千年。这也是他偏好 40 万—20 万年前这一时间窗的部分原因;这给自然选择留下了充足时间。然而,他也承认在那段时间几乎没有递归的证据,因此建议它可能在 4 万年前出现,却没有说明这一过程何时完成。他写道:“上旧石器时代标志着近 3 万年的几乎持续不断的变迁,最终达到了相当于许多当代原住民的现代性水平。”鉴于他强调进化需要时间,而这一过程始于 4 万年前,我将其解读为:现代水平的递归在 3 万年后,即 1 万年前获得。这与 Poulos、Benítez-Burraco、Progovac 和 Renfrew 所建议的时间点相似。这是智性悖论的终点。 ↩︎
用环境因素来解释神经进化相当流行。例如,2016 年的论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组历史》(A genomic histo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发现了选择的信号。他们报告说:在排名靠前的峰值中(扩展数据表 2),我们发现了与甲状腺系统相关的基因(NETO1,在全球扫描中为第七峰,在局部扫描中为第一峰)以及与血清尿酸水平相关的基因(在全球扫描中为第八峰)。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对沙漠寒冷的特异性适应有关39,而升高的血清尿酸水平与脱水有关40。因此,这些基因是适应沙漠生活的潜在候选者。然而,仍需进一步研究,以将推定的受选择遗传变异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特定表型适应联系起来。
然而,许多候选基因也与神经过程相关(如 CBLN2、NETO1、SLC2A12 和 TRPC3)。也许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看看这些是否与象征革命有关。2023 年的论文《澳大利亚原住民基因组结构变异景观》(The landscape of genomic structural variation in Indigenous Australians)同样报告了自与欧亚人分离以来的选择证据。 ↩︎在补充材料中,他们说得更直白一些。第 3.6 节《神经功能作为人类中被低估的适应靶点》:“在 32 个古代欧亚候选基因中,大约三分之一可以被明确赋予与神经功能相关的生理角色(表 1、S6)。我们的时间分析表明,这些神经基因中的大多数(82%;9/11)在约 8 万—5 万年前的阿拉伯停滞期(Arabian Standstill)处于选择之下,其余两个基因(WWOX 和 DOCK3)则紧随其后,在初始上旧石器时代(约 4.7—4.3 万年前)出现。因此,神经适应似乎是阿拉伯停滞期以及早期解剖学现代人(AMH)扩散至欧亚大陆过程中选择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鉴于考古学关于这一时期快速认知发展之建议,这一点再次显得颇具启发性。” ↩︎
最近这篇论文认为,最早的任何形式的象征行为,是在以色列发现的 12 万年前在原牛骨头上刻下的 6 道刻痕。从 10 万年前起,就有零散的埋葬证据。 ↩︎
McKenna 不去看《圣经》并非偶然。他那一代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对西方传统有一个盲点。他花了大量精力从玛雅历法中推算世界末日,却并未给予《启示录》太多重视。先知在本乡本土无荣誉。在论证现实由语言建构、而古代萨满教对此有所理解之后,McKenna 写道:
如果语言被视为认知的首要数据,那么我们在西方就被严重误导了。只有萨满式的路径才能给出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正走向何方?
但《圣经》说得很清楚:太初有道!这是最基础的内容。举一个近期的例子,Jordan Peterson 采访了基督教护教者兼数学家 John Lennox,他的主要论点就是,《圣经》关于宇宙以语言为基础的说法是正确的,而科学此前未能领会这一点。 ↩︎我原本以为眼镜蛇属 Naja 与印度的 Naga 是同源词,但根据维基百科,这一点存在争议。ChatGPT 也在这一点上与我争论。不过好的一面是,如果这篇文章获得足够关注,未来版本的 ChatGPT 将会在训练中读到它,然后就会同意了。SEO 认识论:愿最好的模因获胜。 ↩︎
Hillman 的荣誉提名引文:
“Medea 的仪式性圣餐是由一种特定的 ios(箭毒)与其‘解毒剂’组合而成,后者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 Galene,意为‘平静’。Medea 的 ios 来自一种 ἔχις,这个希腊词对‘蝰蛇’的指称令人沮丧地宽泛。古代医学文献倾向于把所有蝰蛇归为单一的蛇源药物家族;任何蝰蛇物种的毒咬都被简单地视为‘蝰蛇击’。更令人困惑的是,从一位 Echidna 女祭司那里接受圣礼被称为‘被蝰蛇击中’。”
“除了蝰蛇毒、致幻蘑菇与秋水仙之外,Medea 的 ios 还包含著名的‘紫色’,即 πορφυρα,一种从海洋软体动物(骨螺)中获得的纺织染料。”
“Medea 含有秋水仙的复合物也被称为‘普罗米修斯之药’,并与秋水仙的颜色以及骨螺那惊艳的紫色染料紧密相关。” ↩︎我找到好几个博客都提出了这一主张,但遗憾的是没有给出来源。为防止链接腐烂,这里摘录相关段落:“也有人提出,神谕的恍惚状态可能是由蛇毒引发的,尤其是眼镜蛇或银环蛇的毒液,它们被认为具有致幻性,而预言者可能会将其误认为神圣异象。”——摘自博客《Cleopatra’s Affairs Were a Political Gamble… that Failed》。
或者,来自 Root Circle:
“其他迹象强烈表明,神谕者是通过使用蛇毒来诱导恍惚状态的。有确凿证据表明存在蛇崇拜、蛇饲养以及涉及活蛇和神话蛇的占卜仪式。许多神圣神庙与崇拜中心饲养着各种蛇类,由运营神庙的祭司与女祭司照料。
‘在罗马人中,蛇崇拜主要与动物作为守护神(genius)的化身相关,蛇在神庙与住宅中被大量饲养。希腊对蛇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的崇拜很可能影响了罗马人……
这一崇拜更本土化的一面可以在拉努维乌姆(Lanuvium)的蛇洞中看到,处女们每年被带到那里以证明其贞洁。’——《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德尔斐神谕——mutterhood》(The Oracle of Delphi – mutterhood)中。 ↩︎《降临之神:狄俄尼索斯秘仪再探》(The God who Comes: Dionysian Mysteries Revisited),第 34 页
“……得墨忒耳神庙,那里可能饲养着神圣的蛇。已知希腊人饲养并崇敬的物种之一是塞浦路斯猫蛇(Cyprian catsnake),一种可爱的浅褐色生物,身上点缀着紫褐色斑纹,其毒液——对人类本身无害——据说具有精神活性;非洲紫光蛇(African purple-glossed snake)的毒液也被认为有类似效果。所有似乎使用了蛇的秘仪节日,如 Agrai、忒斯摩福里亚(Thesmophoria)与 Arrhephoria 仪式,都可能是为这些神圣爬行动物的喂食时间。”——Rosemarie Taylor-Perry ↩︎《教父著作》,第27页:“那么,如果我来谈论这些秘仪呢?我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阿尔喀比亚德那样,以嘲弄的方式泄露它们,而是要用真理之言,充分揭露隐藏在其中的巫术;而你们那些所谓的神明,那些秘仪所归属的对象,我将仿佛在生命的舞台上,将他们展示给真理的观众。酒神女祭司们为狂乱的狄俄倪索斯举行狂欢仪式,以生食肉类来庆祝她们神圣的狂喜,并在分配被屠宰祭品的肢体时,头戴蛇冠,尖叫着那个将错误带入世界的伊娃之名。巴克科斯狂欢仪式的象征是一条被奉献的蛇。此外,根据对希伯来语词汇的严格解释,经送气处理的名字 Hevia 意味着一条雌蛇。”这与希腊诗人卡图卢斯对一次酒神狂欢的描述相似:
“于是她们到处狂乱地奔走,心神癫狂,疯狂地高喊‘Evoe!Evoe!’,一边剧烈地摇晃着头。有的人挥舞着顶端包裹起来的酒杖,有的人抛掷着被肢解公牛的四散肢体,有的人用扭动的蛇缠绕自身;还有的人庄严地抬着封在匣中的幽暗秘仪,这些秘仪是凡俗之人徒然渴望得闻的。”
——卡图卢斯,《第64首诗》251–264行(译文在 F. W. Cornish《Loeb 古典丛书》译本基础上改编)
“Evoe”是在狂欢仪式中呼喊的词,而克莱门斯认为这意味着“Eve(夏娃)”。需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并不做此联结。词典中说,它是用于巴克科斯庆典中的狂喜呼喊。 ↩︎眼睛同时也是大女神。Robert Clark《古埃及的神话与象征》(Myth and Symbol in Ancient Egypt)第218页:“眼睛是埃及思想中最常见的象征,也是对我们来说最为奇异的一个。Crawford 最近已经表明,新石器时代世界中在亚洲和欧洲的丰饶女神,是以一只眼——或双眼——来表现的。埃及几乎可以肯定处于这一原始‘眼’崇拜的影响轨道之内,但埃及神圣的‘眼’却是如此复杂而独特,以至于目前仍无法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联系起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任何具体情形中她被称为何名,埃及的眼始终是大女神的象征。” ↩︎
引文出自他论文《走出非洲:人类最古老故事的旅程》(Out of Africa: The journey of the oldest tales of humankind)的上下文:“最为显著的是由伟大英雄——天父的后裔——所屠杀的原初巨龙。在印度,是因陀罗杀死了三头爬虫,就像他的伊朗‘堂兄’ThraØtaona 杀死一条三头龙,或者像他们在日本的远方对应者须佐之男(Susa.no Wo)杀死那条八头怪物(Yamata.no Orochi)。在西方,在英格兰,是贝奥武夫;在《埃达》中,是西格尔德,即中世纪《尼伯龙根之歌》(被瓦格纳用于其歌剧)的齐格弗里德,完成了这一英雄壮举。我们还可以比较赫拉克勒斯杀死勒尔纳九头蛇,以及在埃及神话中,胜利的太阳神每晚在地下向东返回、以便再次升起时,所屠杀的‘深渊之龙’。甚至在较近的夏威夷、最早期的中国以及玛雅神话中也有遥远的回响。只有在大地被龙之血液所滋润之后,它才能承载生命。”
他在欧亚大陆与美洲的宇宙起源神话中识别出15个要素。最后几个与蛇崇拜从某个传奇核心(格拉维特文化时期的欧洲?西伯利亚?安纳托利亚?)向各地影响圈扩散的模式相当吻合:
9 首批人类及其(或半神性)最初的恶行;乱伦问题
10 英雄与宁芙/阿普萨拉/女武神
11 杀龙/使用天界饮料
12 带来火/食物/文化
13 人类扩散/地方贵族(“国王”) ↩︎岩画的年代测定十分困难,因为其上没有可用于碳测年的有机物。许多年代是通过将某种绘画风格与某一时期相联系来确定的,然后该风格中的一切作品都被假定为出自那个时期。我对这幅作品年代的一点怀疑在于,它的风格与后面那些相隔数千年的图像极为相似。不过,论证并不依赖这些年代,因此我没有更深入地调查。 ↩︎
参见 Schmidt 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或《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的访谈。 ↩︎
这可以解释为何克洛维斯文化如此迅速地传播到南北美洲,以及先前居民为何几乎没有留下遗传贡献。同样的原因也解释了丹尼索瓦人在亚洲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他们没有递归能力,因此在智人到来时被消灭或同化。 ↩︎
他将时间定在距今16万年的理由是桑族布须曼人的基因分化。新的研究估计这一分化时间为距今30万年;我想知道他是否会据此更新自己的模型,或是允许扩散的可能性? ↩︎
“但霍皮印第安人与活蛇有着亲密的关系,并尊敬它作为化身。他们相信死去的巫师会以牛蛇的形态归来,如果牛蛇被杀,其灵魂便会获得解放。蛇氏族主持古老的蛇舞,这是一年一度为求雨而举行的九日仪式,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举行。仪式的大部分内容是秘密的,但有四天要用来捕捉一种被称为 nuntius 的响尾蛇,这个词意为‘信使’(可以捕到一百条)。在最后一天日落时分,经过洗礼仪式后,祭司们身着神话人物的装束,缓慢地围成一圈起舞,口中叼着活蛇,并不时更换。许多小时之后,祭司们从高地奔向神圣之地,在那里将蛇放生,让它们去向诸神传递信息。”
——Drake Stutesman,《蛇》(Snake) ↩︎例如,仍然崇拜一位美国大兵为神的波利尼西亚崇拜。
在某种意义上,药物会贬低这一观念,使其看起来更像幻觉或迷幻体验。它们可能有助于改变递归状态,但我想明确指出,它们并非必需。在全世界范围内,萨满都会将能量向脊柱上提。这很可能是最初“套装”的一部分,并在印度以昆达里尼(字面意为“蛇”)瑜伽、在美洲以各种蛇舞、在南非以恍惚之舞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萨满教只有大约四万年的历史。当一个陌生人来到村庄,教人们以某种舞蹈或冥想方式进入改变的意识状态时,那会是怎样的体验?即便不包括药物,也会相当震撼。不难理解,这样的教师为何会被记忆为超越凡人的存在。 ↩︎例如,论文《来自北方水域的大地母亲》(Earth Mother from Northern Waters)中报告:“澳大利亚北部原住民的看法十分明确:‘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来自海的那一边。她的家常常被说成是一片遥远的土地。” ↩︎
他的措辞略显尖锐。安达曼人生活在缅甸以南的一串岛屿上。他们常被视为第一波也定居了澳大利亚的人群的文化遗存(例如 Witzel 的观点)。关于他们,Campbell 说:
“最早的安达曼人既不懂制陶,也不养猪。这两者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被引入,而野猪在他们神话中的突出地位表明,与之相关的(新石器或青铜时代的)神话体系也必定在那时一并被带入。陶器逐渐劣化,家猪逃逸成野,而随着大陆技术体系的瓦解,其中若干要素被吸收进当地的狩猎—采集传统之中。”
在将若干安达曼故事与希腊和近东关于大女神的神话联系起来之后,他继续说:
“因此我们不能像 Radcliffe-Brown 那样假定,这些关于猎猪和猪的安达曼故事是真正原生于岛民、且与其文化一样原始。相反,它们是大陆神话体系的碎片,这一体系已经退化——也就是说,像猪本身一样野化,并且像相关的陶器一样劣化,仿佛破碎成一地碎片。”
再看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论述(第132页):“布须曼人是约公元前三万年那场伟大创造性爆发向南延伸部分的最后继承者。” ↩︎这一难题在语言上同样存在。为何澳大利亚诸语言彼此如此相似,却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大相径庭?参见:《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时间、多样化与扩散:语言史前的三个谜题》(Time, diversification, and dispersal on the Australian continent: Three enigmas of linguistic prehistory)。 ↩︎
《古代近东对蛇的认知:其在青铜时代辟邪魔法、治愈与保护中的角色》(Perceptions Of The Serpen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ts Bronze Age Role In Apotropaic Magic, Healing And Protection)。
夏娃的闪语名字是 Hawwa。这个名字在词源上被联系到“蛇”和“生命”这两个词。Wallace(1985:148)指出,早期拉比诠释者已经注意到 Hawwa 与“蛇”之名之间的联系。夏娃与蛇之间的联系,以及她可能是一位蛇女神,甚至本身就是一条蛇的可能性,曾被 Nöldeke、Wellhausen 和 Gressman 等学者探讨(Wallace 1985:148)。更近一些,Wilson(2001:216)认为蛇代表的是 Ašerah。Wilson(2001:210)支持蛇/生命之间的词源联系:“蛇并不是夺取人类生命的代理者;它是生命的守护者……”。
她接着论证,夏娃就是泛迦南的蛇女神“Elat”,她常与睡莲一同出现,而睡莲是芦丁(rutin)的良好来源: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 ↩︎《Nachash 与 Asherah:古代近东中的蛇象征与死亡、生命和治愈》(Nachash and Asherah: Serpent symbolism and death, life, and h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LS Wilson 1999:
“本研究考察了闪语词根 nhš,它既指蛇,也指魔法或占卜的实践。研究表明,nhš 的含义更接近于奠酒祭献,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魔法或占卜。文中考察了 nhš 的语文学起源及其在伊甸园戏剧中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将蛇崇拜与人祭联系起来(我的论点是,人祭源自暴力的蛇毒死亡与重生仪式):
“蛇作为生命、死亡与治愈代理者的角色,在各文化中分别或组合地得到了展示。达罗毗荼传统中缠绕在树上的蛇形形象,体现了生命与丰饶的属性,正如埃及的 Shaï 或 agathós daímón 一样。圣经中那位神秘却无处不在的女神 Asherah,在相关近东祭祀体系中的蛇性特征,既从现有的铭文与图像材料中得到证实,也从新发现的材料中得到印证。从腓尼基、迦太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得知人祭是一种被接受的仪式,因此蛇也就成为死亡的代理者。” ↩︎《蛇的神话与人类的诞生:对原始印欧文化的一种投射》(The Myth of the Serpent and the Birth of Mankind. A Projection into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战斗是彻底的,精神被完全吸纳,恐惧与勇气融为一体,血液在血管中奔涌,有人失去了生命,但这一刻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战士的心灵中发生了一场感官爆炸:在一瞬间,一切都变得清晰——天空、大地、自身的本质、那条蛇、情感、生命与死亡。他的感知洞彻一切。他战胜了那条蛇,他残酷地屠杀了它,毫不留情——自我意识与由心引导的意志力成正比。
战斗结束了,这个人现在可以将所得的意识教给他人,“我在”*h1e’smi,“你在”*h1e’sti。战斗结束了,人类拥有了丰饶的泉源,可以定居下来,并轻松理解自然在生长与死亡中的循环、季节的更替以及种子的功能。他发现了农业、畜牧业、车轮与车辆。阿耆尼(Agni)所代表的火焰,就是从被赎回的泉源中流出的意识,而从今以后,这些泉源将拥有多重形态。” ↩︎“但从我的政治视角来看,对人类起源研究的首要价值在于,它首先表明早期生活是共产主义的(Engels 1972 [1884];Lee 1988)。其次,它告诉我们,革命位于我们存在的核心。”
——Chris Knight,《血缘关系:月经与文化的起源》(Blood Relations: Menstru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e)
“在这方面,我的理论不断演进的核心,或许也是我的模型所引导我得出的最令人兴奋的民族志发现,就是:早期功能主义取向的田野工作者曾将澳大利亚原住民所谓的‘蛇’视为‘性’、‘天气变化’、‘水’、‘阳具’、‘子宫’或其他某种欧洲人熟悉的现成范畴的象征——而这个所谓的‘蛇’根本不是那样的东西。它的意义不是一个事物。它并不指涉人类主体之外的某种外在对象。我在最初的理解曙光开始照进来时得出的结论是:它是纯粹的主体性。它是团结。它是我的阶级斗争。它是纠集在一起的罢工纠察线,是血红的旗帜,是多头的反抗巨龙。它是对灵长类资本主义的推翻——是建立文化领域的伟大性罢工的胜利。”
——《血缘关系》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他的时间框架,我们大致一致:“我认为,这种多层次的社会性与心智分享的高度强度——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所说的‘文化’即指此物——最早不过是在距今九万年、而更可能是在距今四万至四万五千年前才被普遍而稳定地实现(Binford 1989;Trinkaus 1989)。我也认为,它的出现并非渐进式的,而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性与政治爆发——正如它被称为‘创造性爆发’那样(Pfeiffer 1982)。”
——《血缘关系》 ↩︎参见 Robert Clark《古埃及的神话与象征》。第76页:“这是否意味着,天地的分离、历法时间的开端,标志着向男性至上的转移?”从男性视角看,或许如此。只有在递归(此处以二元性与时间为标志)在男性中已成第二天性(甚至第一天性?)之后,他们才能接管主导权。
“迄今为止,高神与原初之水一直被视为男性或双性。但还有另一种传统,即关于一位母神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古王国时期可能被忽视或压制,却在棺椁文中浮现出来,因为中央权力的削弱使地方崇拜得以进入文本。”(第87页)
第226页将蛇、第三只眼与大女神主题结合起来:“王冠、眼镜蛇与母神(‘大物质’)是一体的。我们记得,愤怒的眼变成了眼镜蛇,而拉将其缠绕在头上,这就是第一次加冕。在水中,眼来自高神,因此他是它的始祖。眼同时也是母神,因为当眼发怒时,人类皆从它的眼泪中诞生。因此,国王之母——或原初之母——就是眼。但由于眼是装饰王冠并成为其一部分的眼镜蛇,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同一位女神既能点缀国王的额头,又能同时作为他的母亲。这本应已足够复杂,但即便如此,这段祈祷还有进一步的象征等同。或许有两只眼,一只在原初之水中,另一只在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中;但它们同样是一体的。国王是为王冠——即眼——而战的荷鲁斯,他在与塞特的争斗中先是失去了自己的真实之眼,随后又重新获得。”
需注意,这并非一位女性主义学者,书的主题也不是大女神或原初母系制。与 Dunbar 一样,这些诠释出自具体领域的专家。 ↩︎这种“杠杆”被极为有效地使用。例如,试着让谷歌的 Gemini 生成一张白人的图像。 ↩︎
Julian Jaynes(“二分心智”理论提出者)和 Ian McGilchrist 都在意识问题上提到过大脑侧化。性别差异十分显著:“男性大脑在半球内连接方面得到优化,而女性大脑则在半球间连接方面得到优化……这些观察表明,男性大脑的结构有利于在知觉与协调行动之间建立连接,而女性大脑则被设计为有利于在分析性与直觉性加工模式之间建立沟通。” ↩︎
根据 UniProtKB 基因摘要,TENM1:“在边缘系统神经可塑性的调节中发挥作用。”并且“在神经元中诱导 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转录抑制。”(BDNF 类似于蛇毒中发现的神经生长因子。)
其他研究发现,TENM1 与某些具有年龄依赖表现特征的癫痫类型相关。鉴于我认为癫痫与递归有关,并且它过去往往在较晚年龄才发展出来,这一点令我颇感兴趣。(需注意,其他人也曾将癫痫与产生意识的递归认知结构的崩解联系起来:参见《癫痫与递归意识,特别关注 Jackson 的意识理论》(Epilepsy and Recursive Consciousnes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Jackson’s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根据人类基因数据库,TENM1 在腹侧被盖区(VTA)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中优先表达。这些神经元与胆碱能系统相互作用,而后者是大脑行为奖赏系统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尼古丁之所以如此容易上瘾,是因为它劫持了这一系统(1,2)。蛇毒同样以胆碱能系统为靶点,尽管现实中这与 TENM1 已相隔多重环节。
一份区分现代人与古人类的单核苷酸变异目录(补充材料)将功能相关的 TENM4 列入将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及丹尼索瓦人区分开的基因名单中。 ↩︎《焦虑的欢愉:亚马孙人群的性生活》(Anxious Pleasures: The Sexual Lives of an Amazonian People,1973)
“[父权社会秩序]并非一直如此,至少在神话中不是。我们被告知,古时的女人(ekwimyatipalu)是母系族长,是如今男子会所的创立者,也是 Mehinaku 文化的创造者。Ketepe 是为我们讲述这则辛古‘亚马逊女战士’传说的叙述者。
女人发现长笛之歌
在古时,很久以前,男人们独自生活在一处遥远的地方。女人们离开了男人。男人完全没有女人。可怜这些男人,他们只能用手来行房。男人在他们的村庄里一点也不快乐;他们没有弓,没有箭,没有棉线臂环。他们连腰带都没有。他们没有吊床,只能像动物一样睡在地上。他们通过潜入水中、用牙齿叼鱼来捕鱼,就像水獭一样。为了烤鱼,他们把鱼夹在腋下加热。他们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任何财物。
女人的村庄则完全不同;那是真正的村庄。女人们为她们的首领 Iripyulakumaneju 建造了村庄。她们盖房子;她们系腰带和臂环,绑膝带,戴羽毛头饰,就像男人一样。她们制作了 kauka,第一支 kauka:“tak…tak…tak”,她们从木头中将它刻出。她们为 Kauka 建造了房屋,第一个灵之居所。哦,那些古时圆头女人真是聪明。
男人看见女人在做什么。他们看见她们在灵屋里吹奏 kauka。“啊,”男人说,“这不好。女人偷走了我们的生命!”
第二天,首领对男人们说:“女人不好。我们去找她们。”
从远处,男人们听见女人们在灵屋里吹奏 kauka、唱歌跳舞。男人们在女人村庄外制作了牛吼器。哦,他们很快就要和自己的妻子行房了。
男人们靠近村庄,“等一等,等一等,”他们低声说。然后:“现在!”他们像野印第安人一样向女人们扑去:“Hu waaaaaa!”他们呼喊着。他们挥动牛吼器,直到它们发出像飞机一样的声音。他们冲进村庄,追赶女人,直到抓住了每一个,直到一个也不剩。
女人们怒不可遏:“住手,住手,”她们喊道。但男人说:“不好,不好。你们的腿带不好。你们的腰带和头饰不好。你们偷走了我们的图案和颜料。”男人们扯下女人们的腰带和衣物,用泥土和带皂性的树叶擦洗她们的身体,以洗掉那些图案。男人们训斥女人:“你们不佩戴贝壳 yamaquimpi 腰带。来,你们戴麻线腰带。我们才是涂装的人,不是你们。我们才是站出来发表演说的人,不是你们。你们不吹神圣的长笛。那是我们做的事。我们是男人。”
女人们跑回自己的房子躲藏。所有人都藏了起来。男人们关上门:这扇门,那扇门,这扇门,那扇门。“你们只是女人,”他们喊道。“你们纺棉。你们织吊床。你们一早公鸡一打鸣就开始织。吹 Kauka 的长笛?那不是你们的事!”
那天夜里,天黑之后,男人们来到女人那里并强暴了她们。第二天早晨,男人们去捕鱼。女人们不能进入男子会所。在那古时的男子会所里。第一个会所。”
这则 Mehinaku 关于“亚马逊女战士”的神话,与许多拥有男子宗教团体的部族社会所讲述的故事相似(参见 Bamberger 1974)。在这些故事中,女人是最初拥有男人神圣物品(如长笛、牛吼器或号角)的人。然而,女人往往无法照料这些物品,或无法供养它们所代表的灵体。男人们便结成同盟,欺骗或强迫女人放弃对男子宗教团体的控制,并接受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些神话中惊人的相似性?人类学家一致认为,这些神话并非历史。讲述这些神话的民族在过去很可能与今天一样是父权制社会。这些故事不是通往过去的窗口,而是活生生的叙事,反映了对一个民族性别认同观念至关重要的思想与关切。
Mehinaku 的传说以古时男人处于“类动物”的前文化状态开篇。与许多其他神话以及 Mehinaku 对女性智力的普遍看法相反,女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建筑、服饰与宗教的发明者:“那些古时圆头女人真聪明。”男人的上升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实现的。他们像“野印第安人”一样发起攻击,用牛吼器恐吓女人,剥夺她们的男性装饰,将她们赶进房屋,强暴她们,并向她们灌输适当性别角色行为的基本准则。 ↩︎《启蒙礼仪与象征:诞生与重生的奥秘》(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The Mysteries of Birth and Rebirth,1958)
“在塞尔克南人中,青春期启蒙礼早已被转化为一项专门为男性保留的秘密仪式。一则起源神话讲述,在最初——在月亮女人、强大女巫 Kra 的领导下——女人因为懂得如何将自己变成‘灵’,懂得制作和使用面具的技艺,而恐吓男人。但有一天,太阳男人 Kran 发现了女人的秘密,并将其告诉了男人们。男人们大为震怒,杀死了所有女人,只留下小女孩。从那时起,他们便组织秘密仪式,以面具和戏剧化的仪式来反过来恐吓女人。这个节日持续四到六个月,在仪式期间,邪恶的女性灵体 Xalpen 折磨启蒙者并‘杀死’他们;但另一位灵体 Olim,一位伟大的巫医,又将他们复活。因此,在火地岛,如同在澳大利亚一样,青春期礼仪趋向于变得愈发戏剧化,尤其是强化了启蒙性死亡场景的恐怖性质。” ↩︎尽管人们可能会问:“那么,欧洲的女巫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事?” ↩︎
前两页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为了让人了解关于牛吼器的文献有多庞大,我在下面将不同部族加粗标出。在离开“性与结社”这一主题之前,我必须简要处理一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民族志上具有极高兴趣的话题。在对澳大利亚启蒙仪式的概述中,曾提到过牛吼器,这是一种会发出嗡嗡声的乐器,对女性是禁忌。人们极力防止未入会者得知这些怪异声音其实是由这样一个简单装置发出的,这种谨慎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仿佛所有神秘事物的精髓都集中在制造这种呼呼声上,好像从土著的观点看,漫长仪式中所有的纷扰与痛苦,都在男孩被告知如何让一小片木板在空中呼啸而过的那一刻达到高潮。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凡是发现这一秘密的女人,以及泄露秘密的男人,都要被处以死刑。但更为惊人的是,在世界不同地区竟然出现了同样的观念联想。下面的若干例子足以作为说明。 ↩︎
事实上,洛维在发展当今人类学中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实践中,这一立场往往淡化扩散的重要性。文化相对主义者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例如,牛吼器在希腊和澳大利亚具有不同的意义)、独立发明,以及对宏大理论的一般性怀疑(除了,呃,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因此,他在这一实例中对扩散的支持,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权宜之计。 ↩︎
我想以澳大利亚为重点回到这个话题。Pama‑Nyungen 语系的扩张看起来很像蛇崇拜的传播。请看一篇由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团队撰写论文的摘要: ↩︎
例如,奥丁为学习卢恩文字而作出的牺牲: ↩︎
[图像:原帖中的视觉内容]
Göbekli Tepe 不同石柱上描绘的蛇。它们常常被画在蚂蚁或蝎子旁边(更多例子见这篇论文)。这可能与蜕皮/蜕外骨骼有关,但我认为毒液是更可能的统一因素。既然有些故事可以流传一万年之久,那么这一崇拜的神学某些方面也可能渗入了我们的文化。我喜欢这样想象主持仪式的人鼓励入会者说:“蛇要伤你的脚跟,你却要伤它的头。” ↩︎下面是一个近期的例子,来自一位进化生物学家回答“我们何时成为人类”这一问题时的说法: ↩︎
它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前之前,具有人类智慧特征的行为并未被广泛表现出来?在为 EToC 做研究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智慧悖论”(Sapient Paradox)。在产生 EToC 这一想法之后,我最初的念头是,《创世记》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必定在一个神话能够存续的时间尺度之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得像人类了。发现至少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具有人类智慧的行为是近期才出现的”,而且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这让我大为震惊。同样,我原本也不认为会有任何关于蛇毒作为致神剂(entheogen)的证据,事实上,我在写《蛇崇拜》和 EToC 第二版时,并没有任何证据。结果发现,它很可能在厄琉息斯被使用,现在在印度仍在使用,或许在美洲也曾被使用。同样,我从未听说过“双脑解体”(Bicameral Breakdown)。至少从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看,EToC 在其所做预测方面有着相当出色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