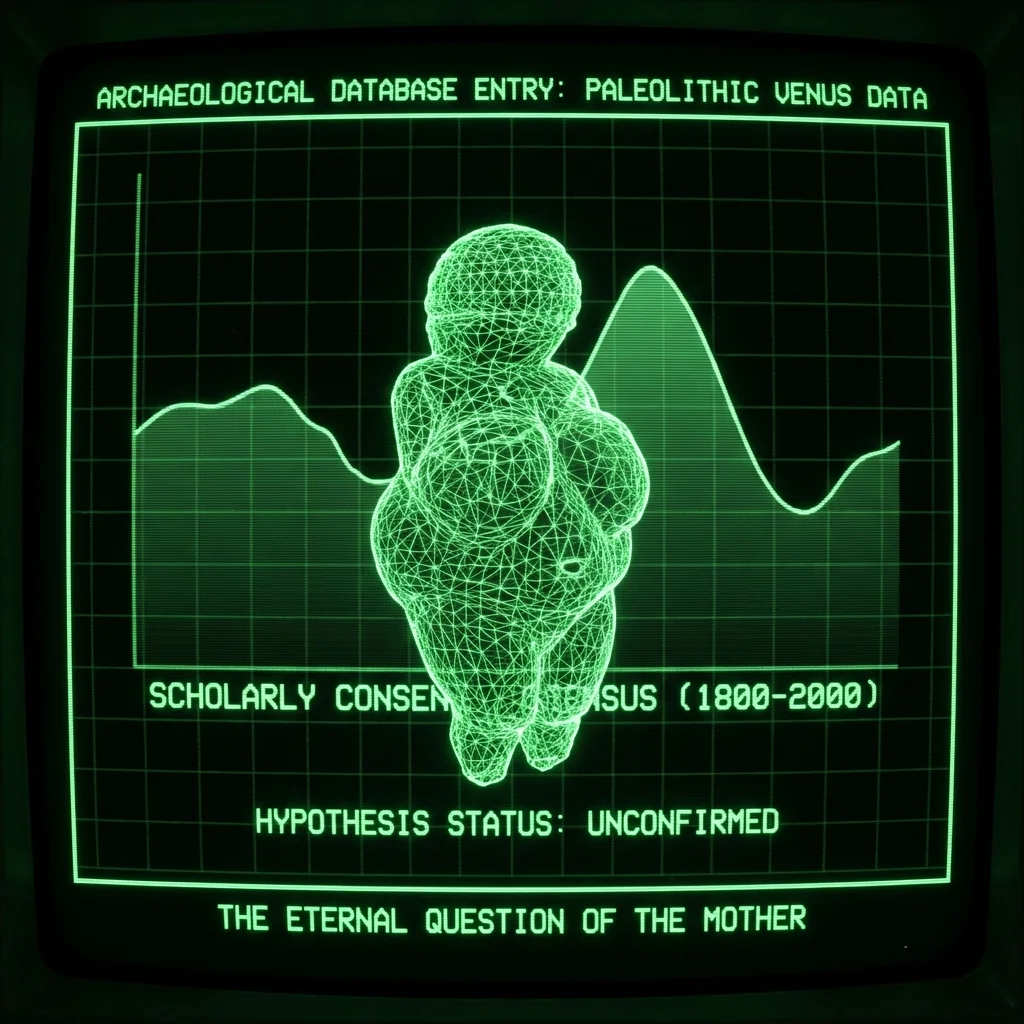摘要
- 世界神话中常常描绘女性创世者,这推动了关于古代母权制(女性统治或女性居于中心地位)的理论。
- J.J. 巴霍芬(Bachofen,1861)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母权”(Mutterrecht)阶段,影响了恩格斯、女权主义者,甚至部分纳粹意识形态家,但其理论往往主要基于对神话的诠释。
- 19、20 世纪的人类学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如摩尔根支持母权阶段,而梅因、韦斯特马克以及后来的马林诺夫斯基则提出批评,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存在女性政治统治。
- 第二波女权主义重新激活了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如金布塔斯提出的“旧欧洲”),但也遭遇学界批评,强调缺乏证据以及其他解释路径(如班伯格认为许多“母权神话”实际上是在为父权制辩护)。
- 当代研究更多聚焦于女性在现实中可见的贡献(祖母假说、协同育儿、通过“母语式”语调推动语言起源、在创新/农业中的潜在角色)以及灵长类类比(倭黑猩猩),而非字面意义上的母权制。共识是:尚无被证实的母权社会,但女性是关键的文化塑造者。
神话与宇宙论中的女性创世者#
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体系中,女性常常作为原初的创世者或文化带来者出现。以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境时代”(Dreamtime)叙事为例,一些祖先姐妹被认为确立了法律与仪式。阿纳姆地的 Wawilak 姐妹被说成“为最初的人们奠定了大部分法律与仪式”,教给他们一直延续至今的道德规范。在旅途中,这些姐妹为土地命名并创造神圣仪式,从根本上在约隆古(Yolngu)传统中奠定了文化的关键要素。类似主题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在纳瓦霍宇宙论中,“变换女人”(Changing Woman)是核心人物,她生下双胞胎文化英雄,并帮助塑造“地表之民”(Earth Surface People)的世界,将秩序和新的存在引入创世过程。在日本神道传说中,太阳女神天照不仅体现了赋予生命的太阳力量,而且在神话中是皇室血统的女祖先;传说第一位日本天皇是她的后裔,这标志着社会权威具有神圣的女性起源。
这些神话表达了一种将女性视为生命与法律的生成者的观念。许多早期社会将大地或生育人格化为女性——从“旧欧洲”的大母神到各类原住民传说中的“第一位女人”形象。史前艺术也暗示了类似观念:旧石器时代“维纳斯”小雕像的大量存在,使一些学者假设存在一种远古的母神崇拜,认为早期人类尊崇女性的创造性原则,将其视为文化与共同体的源泉。尽管解释各异,这类神话与象征性证据为后来的理论家铺垫了基础,使他们设想女性曾在社会中实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孕育出最早的人类制度。
巴霍芬的《母权》:母系史前时代#
现代学术界关于“女性作为文明创始者”的观念始于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1861 年的开创性著作《母权》(Das Mutterrecht,“Mother Right”)。巴霍芬是一位瑞士法学家与古典学者,他提出,人类社会在父权制之前曾经历过一个早期的“女性统治”(gynecocracy)阶段。他认为,在人类原始时代,普遍存在着“杂交婚”或“群婚”(Hetärismus),因此父系血缘难以确定,血统与继承只能通过母亲来追溯。依巴霍芬之见,这导致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母权”(Mutterrecht)时期,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唯一可确证的父母,享有崇高的荣誉与权威。他相信,“最初的人类社会是母权制的,并以广泛的性放任为特征,这在对女性神祇的崇拜中有所反映”。他将神话视为社会进化的化石记录,坚持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发展阶段的活生生表达”。例如,他把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中俄瑞斯忒斯因弑母克吕泰涅斯特拉而受审的情节,视为古代母权被父权推翻的象征。(在剧中,新神阿波罗与雅典娜站在俄瑞斯忒斯一边,合法化了“父系血统比母系更重要”的原则,从而寓意父权的胜利。)巴霍芬还援引了关于异族风俗的记载(例如,他注意到小亚细亚吕基亚人中存在母系亲属制度),以及考古中的女性象征。基于这些材料,他构建出一个宏大的文化阶段演化图式:从混乱的“群婚”(Hetärismus)中产生出一个以大地与生育为中心的母权时代(以农业与女神崇拜为典型),而这一时代最终被父权秩序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巴霍芬将母权时代理想化为和平与社会和谐的时期。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的母权时期具有崇高的伟大”,在这一时期女性的价值观占据主导:母亲激发“贞洁与诗意”,追求和平与正义,同时驯服男性“野性、无法无天的阳刚”。他认为,这一女性原则神圣化了家庭与社会,直到被更具攻击性的男性原则所取代。巴霍芬富有感染力(尽管带有高度推测性)的著作,将向父权制的转变描绘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例如,他写道,在希腊神话中,正是新兴父权神祇的降临——一种神圣干预——才“完成了推翻母权的奇迹”,并确立了父权。
巴霍芬的理论在当时大胆而非正统。他依赖对神话的直觉式解读,并声称传说保留了对史前社会现实“真实但扭曲”的图景,这令更重视经验的学者感到不安。芬兰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在《人类婚姻史》(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1891)中拒绝了巴霍芬的方法,他对“巴霍芬认为神话与传说保存了一个民族‘集体记忆’”这一想法感到“困扰”。
尽管如此,《母权》播下了一颗种子,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好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巴霍芬“创造了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人类与文化发展理论”,虽然最初并不受重视,但后来在德国被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等各种意识形态阵营所吸收。
进化人类学与母权之争(1860s–1900s)#
巴霍芬的论题出现之时,人类学与社会理论正致力于为人类制度构建进化框架。19 世纪晚期,一批重要学者在构建社会进步的宏大理论时,要么接受要么反对“远古母权制”的设想。
一方面,巴霍芬在早期人类学家与社会理论家中找到了热情支持者,他们正寻求文化进化的普遍阶段。美国民族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研究易洛魁人著称——独立得出结论,认为史前社会最初是围绕母系氏族组织的。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中,摩尔根记录了许多原住民如何通过母亲来追溯亲属关系,并提出原始人类实行群婚,使得母亲成为唯一确定的父母。他在美洲原住民的“分类亲属制度”中看到线索,认为在早期,“通过女性血统的继嗣”是常态,先于一夫一妻制与父系继嗣的兴起。摩尔根基于证据的方法(利用来自易洛魁人、波利尼西亚人等的民族志资料)为巴霍芬的直觉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撑。他因此确信,父权的一夫一妻家庭是人类历史上相对晚近的发展,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母系氏族组织”时代。
英国人类学家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同样在 1865 年与 1886 年的著作中主张早期社会具有母系继嗣;他创造了“族外婚”(exogamy)一词,并提出抢婚与女性稀缺导致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间接暗示了先前存在母权制度。麦克伦南最终将“母系血统为原初形态”的洞见归功于巴霍芬。甚至《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作者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 Frazer)也对这一观念着迷——他致力于汇集全球关于母权的证据,试图用比较民俗与神话来强化巴霍芬的主张。
或许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采纳了原始母权的观念,并将其编织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中,恩格斯大量借鉴了摩尔根(他称赞摩尔根发现了家庭的“史前史”)以及巴霍芬的洞见。恩格斯断言,母权的覆灭与私有制的兴起密切相关。他认为,在部落公社社会中,女性地位相对较高,但随着财富积累、父系血统对继承的重要性上升,男性夺取了控制权。恩格斯那句著名的话是:“母权的推翻是女性性别的世界历史性的失败……die Frau wurde entwürdigt, geknechtet, … bloßes Werkzeug der Kinderzeugung。”在恩格斯看来,这一对女性的“失败”开启了第一种不平等(性别之间),随后又被阶级分化进一步叠加。他将父权制的出现与可继承财产的产生以及为确保父系血统而设计的一夫一妻婚姻联系起来。
恩格斯的戏剧性表述使母权假说在左翼与女权圈子中广为流传,也牢牢将“史前母权”的信念与特定政治解读捆绑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原始母权代表一种早期的公社、平等社会形态,后来被阶级社会所摧毁。这种政治化有时掩盖了经验证据。正如人类学家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后来所言,恩格斯等人过于沉迷于摩尔根与巴霍芬的愿景,以至于“母权时代的历史现实”常常被假定存在,而非被真正证明。
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强烈质疑原始母权的观念。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早在 1861 年就坚持认为,最早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父权家庭,而非母权氏族。梅因出身古代法学背景(并受罗马“家父权”(patria potestas)形象影响),主张父权权威与父系亲属关系是原初的。他将巴霍芬之类的理论视为与罗马法律史和《圣经》相悖的“浪漫故事”。1891 年,韦斯特马克在其关于婚姻的广泛研究中同样得出结论:尽管母系亲属在许多文化中很常见,但并无坚实证据表明曾存在一个女性统治男性的时代;他试图“重建梅因关于人类起源的父权理论”,并否定巴霍芬的神话证据。到 20 世纪之交,大量人类学家对任何社会曾是严格意义上的母权制(即由女性进行政治统治)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随着民族志资料的增多而愈发强烈。
20 世纪早期的发展:从女神崇拜到批判#
在 20 世纪之初,母权假说一方面被新证据加以修正,另一方面也受到新兴社会科学的攻击。在支持的一方,古典学家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及“剑桥仪式学派”(Cambridge Ritualists)将巴霍芬的思想应用于古希腊文化。哈里森认为,前希腊(pre-Hellenic)时期的希腊社会以女神崇拜和或许母系继嗣的社会习俗为特征。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1903)与《忒弥斯》(Themis,1912)等著作中,她主张许多奥林匹斯神话与仪式(如得墨忒耳崇拜、亚马逊故事等)保留了早期母权或至少“以母为中心”(matrifocal)的时代痕迹。她对希腊艺术与神话的解读,提出在后来的男性主导万神殿之下,存在一个情感性、共同体性、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底层。哈里森甚至将古希腊早期文化描述为一种被后期入侵者推翻的“母权”,与巴霍芬的进化叙事相呼应。这引发了更保守的古典学者的反击:如刘易斯·法内尔(Lewis Farnell)和保罗·肖里(Paul Shorey)等学者尖锐批评哈里森,他们的措辞往往带有当时的性别偏见。他们将她的母权观点斥为幻想,并指责她沉溺于所谓“性自由的希腊主义”(sex-freedom Hellenism),把她的学术理论与“女性解放”这一当时被视为丑闻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类反应显示出争论如何与当时的社会态度交织——在女权参政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哈里森的工作实际上被当作对古典学术的女权主义颠覆而遭到攻击。
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文化创始者”论题最雄心勃勃的延伸,或许是罗伯特·布里福特(Robert Briffault)的《母亲们:情感与制度起源研究》(The Mothers: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entiments and Institutions,1927)。布里福特是一位出生于法国的英国人类学家,他汇集了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志实例,主张几乎所有文明的基本方面都起源于母性领域。他断言,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由女性的贡献所塑造:在他看来,家庭本身就是“女性本能的产物”,女性是最先创造社会纽带的人。布里福特将原始母权定义为:不一定是女性在政治上统治男性,而是女性在社会上居于中心并在文化上具有创造性。他例如推测,最初的仪式与宗教崇拜由女性发展而来——注意到月亮女神与月经禁忌在全球范围内的显著地位,他得出结论:女性作为“月亮崇拜的第一批启示者”(the first hierophants of lunar cults)掌握了早期的精神权威。他还提出了“布里福特法则”(Briffault’s Law),其通俗表述为:“在动物家庭中,决定一切条件的是雌性而非雄性。若雌性无法从与雄性的结合中获得利益,则不会发生这种结合。”换言之,持久的家庭或社会单位是围绕雌性的需求与选择形成的。(布里福特澄清,他描述的是动物,并非声称人类社会与动物后宫完全相同。然而,其含义是:人类家庭起源于母性主动——只有在雄性对群体有用时,雌性才允许其加入。)
布里福特的著作大胆宣称,文明是由女性发明的,从婚姻、烹饪到法律与宗教皆然。这直接挑战了当时主流叙事,即认为男性活动(如狩猎或制工具)推动了进步。然而,当时主流人类学界并不信服。到 1920 年代末,社会人类学正转向功能主义,并对单线进化论持怀疑态度。曾研究母系特罗布里恩岛民的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对布里福特的结论提出质疑。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即便在没有生物学父亲概念的社会中(特罗布里恩人认为孩子由祖先灵魂受孕),男性也远非无足轻重——母舅与丈夫在群体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 1930 年代与布里福特展开辩论,主张早期人类家庭很可能始终包含重要的男性贡献,而所谓“以母为中心”的阶段被夸大了。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分析中,没有已知社会赋予女性排他性的权力;真正变化的是血统通过母系还是父系来追溯,而非“女性统治男性”的全面母权。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进化模型。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在 1930 年代提出文化起源的多线模型:他认为,根据不同生态因素,史前文化大致有三种主要类型——母系、父系与父权制。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认为,女性在早期植物栽培中的角色可能提升了她们的地位,并在某些地区促进了女神崇拜。这与现代一些理论相似,即认为女性很可能开启了农业(作为采集者驯化植物),并发明了诸如纺织与制陶等重要技术,从而推动了新石器革命。尽管施密特的著作如今鲜少被引用,但它显示出一种尝试:在讲述文化起源时,将性别与环境因素一并纳入,而非假定一个单一、普遍的母权时代。
到 20 世纪中叶,随着新民族志证据的累积,多数人类学家对母权假说采取批判立场。对部落社会的调查未能发现任何无可争辩的女性主导政治体系的例子。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 1924 年宣称,“母系氏族并不等同于母权制”——即母系亲属制度不应与女性对男性行使权威混为一谈。1930 年,E.E. 埃文斯-普里查德(E.E. Evans-Pritchard)甚至提出,整个“古代母权阶段”的观念是男性幻想(或焦虑)的产物,而非历史现实。尽管如此,“失落的女性主导时代”的想象仍然具有吸引力,并很快在不同意识形态语境中获得新生命。
意识形态与诠释:原初母权的政治#
由于关于女性在文化中是否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直指权力与身份的根本议题,它自始便与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对母权论题的反应往往折射出时代精神——从维多利亚父权社会,到纳粹德国,再到第二波女权主义。
坚持父权规范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家与社会理论家,是最早反对母权模型的人群之一。前文提到的梅因的父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对现状的辩护:它与《圣经》中族长叙事相契合,也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将男性权威视为自然且原初的观念。当巴霍芬与摩尔根的研究开始流传时,一些保守学者将其视为威胁。认为父系血统是晚近发现、早期社会尊崇女性血统的观念,与基督教与维多利亚时代关于上帝赋予父亲角色的信念相冲突。正如一部 20 世纪初的参考著作尖刻地写道,作为发展阶段的母权概念“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这一术语本身就具有误导性。这类否定表明,当时学术主流已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一观念——这或许不仅出于经验层面的理由,也因为它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叙事。
在德语世界,巴霍芬的著作在 20 世纪早期获得复兴,并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思想家中找到出人意料的崇拜者。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转折:即便在公开颂扬雅利安男性、将女性局限于“Kinder, Küche, Kirche”(孩子、厨房、教堂)的国家社会主义语境中,一些纳粹知识分子仍对古代母权神话颇感兴趣。学者指出,“母权神话”具有奇特的政治“双手性”:既能吸引极左(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也能吸引极右。在 1920–30 年代的德国,各类“民族主义-民俗”(völkisch)作家挪用巴霍芬。例如,纳粹重要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aeumler)在印欧过去中看到阳性与阴性原则的协同;他承认史前存在一个“女性统治”(gynæcocracy)时期,但将其塑造为现代性别秩序的高贵对照。他与巴霍芬一样认为,女性独立曾经真实存在,但被男性领导“正当地”克服——然而他也暗示,复兴母权过去的精神理想可以振兴民族。另一个例子是纳粹党首席意识形态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他在《二十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30)中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提及原初母权:罗森伯格设想了一个失落的雅利安黄金时代,这一时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母权制,但他强调古代“北欧”民族中女性与母亲象征的崇高地位。纳粹的母权理论拥护者从未将其表述为“女性统治男性”;相反,他们理想化“日耳曼母性”,将其视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滋养核心。实际上,他们借古代的权威来美化母性——但仅限于严格平衡的性别秩序之内,在这种秩序中男性战士地位仍然占优。
需要指出的是,纳粹对这些观念的兴趣是边缘且自相矛盾的。第三帝国的总体立场是父权与男性支配是自然的(希特勒与希姆莱显然不相信女性在社会上居于首位)。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写,“尽管政权颂扬雅利安男子气概,巴霍芬关于母权的思想仍在纳粹领导层中找到拥护者。”这一悖论说明母权叙事的可塑性:在纳粹手中,它被扭曲为强化一种反动的理想——女性作为被颂扬的母亲,却在政治上从属。到二战结束时,这类观念在官方话语中基本消失,被与纳粹神秘主义与民粹伪史的关联所玷污。
在苏联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母权理论则有不同的命运。恩格斯的权威使“原始母权(及其覆灭)”在 20 世纪早期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苏联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遵循恩格斯,讲授一套社会阶段序列:带有母权的原始公社主义,然后是带有父权的阶级社会,最终是恢复平等的未来共产主义。在实践中,苏联 1920–50 年代的研究确实在苏联境内外各民族中寻找母系氏族的证据,并常常强调那些符合摩尔根–恩格斯框架的发现。然而,他们并未真正声称这些群体中女性统治男性——更强调的是公社式社会结构,而非女性支配。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一叙事的政治功用显而易见:它强调现代父权制(进而资本主义)既非永恒也非自然,而是一种可以被推翻的历史发展。然而,到 20 世纪后期,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叶韦利娜·B·巴甫洛夫斯卡娅(Evelina B. Pavlovskaya)也开始承认,“经典母权制”从未被文献证实存在,他们转而谈论早期社会中的相对平等。
在 1970 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史前女性中心时代”的观念获得了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学术审视。许多女权作家、艺术家与活动家受到“古代女神文化”愿景的鼓舞,在这种文化中,女性拥有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缺乏的自主与尊重。考古发现与重新诠释为此提供了助力。尤其是立陶宛裔美国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提出了“旧欧洲”(Old Europe)的概念,即公元前约 7000–3000 年间巴尔干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明,她将其描述为崇拜女神、平等且“母性中心”(matristic)。金布塔斯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女性小雕像,她辨识出一些符号,并认为这些符号表明存在一种盛行的母神宗教。在她看来,这些旧欧洲社会和平且以女性为中心,直到印欧游牧民族——父权战士——入侵并强加男性主导秩序。金布塔斯谨慎地避免直接称这些文化为“母权制”(matriarchal),更偏好“以女性为中心”(woman-centered)或“母性中心”(matristic)等术语,因为她并未声称女性在形式上统治男性。然而,她的工作被许多女权主义者视为证据,证明父权制并非一贯常态。
与此同时,Elizabeth Gould Davis(《The First Sex》,1971)和 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1976)等作者的畅销书,则生动描绘了一幅失落的母系制与女神宗教的黄金时代图景。她们借助 Bachofen、Briffault 和 Gimbutas 等人的研究(再加上一剂富有想象力的重构),论证女性是最初的文明化力量——发明了农业、文字、医学,并以和平方式进行统治——直到男性的暴力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些作品与女权灵性运动产生了共鸣,推动了 20 世纪晚期女神灵修与新异教实践的兴起。对某些人而言,相信在遥远的过去曾经存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神来崇拜”、社会不受男性支配的时代,是一种极具力量感的体验,它为父权制提供了一个神话性的反叙事。在某些女权主义圈子中,这种“母系史前时代”几乎成为一种教条,被用来想象另一种未来。正如历史学家 Cynthia Eller 所指出的,“在某些女权主义圈子里,我所称的母系史前神话已经作为政治教条而占据主导地位;在另一些圈子里,它提供了思想资源;再在另一些圈子里,它则成为一种新宗教的基础。”
然而,这种热情的复兴也引发了学界的批判性回应,其中包括许多担心一厢情愿式幻想的女权学者。早在 1949 年,Simone de Beauvoir 就对母系乌托邦的设想泼了冷水。在《第二性》中,Beauvoir 将原初母系制的假说斥为“les élucubrations de Bachofen”——即“Bachofen 的胡思乱想(荒谬的胡言乱语)”。她和其他 20 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如法国人类学家 Françoise Héritier)认为,尽管女性神祇或母亲象征十分常见,却没有证据表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史前时代曾经统治过。1974 年,人类学家 Joan Bamberger 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题为《The Myth of Matriarchy: 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母系神话:为何男人在原始社会中统治》),她考察了亚马孙部落中关于女性曾经掌权的神话。Bamberger 发现,这些故事是由男性讲述的警示性叙事——用来教导人们:当女性掌权时,她们会滥用权力,从而为当下男性必须统治提供正当性。她的结论是,所谓母系时代是男性创造出来的神话,反映的是对女性自主性的焦虑,而非对历史记忆的保存。这与早期功能主义的解释相呼应:与其说这些关于女性统治的神话是某个真实过去的证据,不如说它们服务于当下的社会目的(往往是通过展示“女人当家”所带来的混乱来强化父权制)。
到了 20 世纪晚期,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形成的学术共识是:在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在严格意义上是母系制,即女性作为一般规则在政治上对男性行使权威。许多平等主义或母系继嗣社会确实存在,但它们并不是“女性统治”的镜像文化。正如 Wikigender 百科全书简明指出的那样,“母系制”这一术语本身变得有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 Bachofen 的阶段序列模型“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即便是史前女性理论的支持者,如 Gimbutas,也避免使用“母系制”一词,因为它暗含女性支配的意味,而是选择更为细致的术语(如“matrifocal”(母性中心)、“gynocentric”(以女性为中心)等)。尽管如此,在学界之外,失落的母系天堂的想象已经进入大众想象和女权意识之中。它激发了关于女性在进化与历史中角色的宝贵讨论,尽管缺乏关于“母亲时代”的具体证据。
重新聚焦证据:人类学、生物学与语言#
近几十年来,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将讨论引向经验记录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女性在人类故事中贡献的内容。学者们不再问“是否曾经存在母系制?”,而是探究个体女性及女性主导的活动如何在人体进化和文化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路径从意识形态的两极化转向更基于证据、也往往更细腻的理解——一种即便不提出宏大的女性统治主张,也承认女性在史前时代是积极行动者的理解。
灵长类学通过考察我们的猿类近亲,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启发性(也颇具谦卑意味)的背景。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进化模型主要基于对普通黑猩猩的观察——那是父权制、好斗、雄性结盟的社会,雄性支配并甚至残暴对待雌性。这强化了这样一种假设:人科动物的“自然”状态就是雄性支配,早期人类生活在“男人—猎人”式的群体中。但倭黑猩猩(Pan paniscus)的发现与研究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观点。从 1990 年代开始,灵长类学家 Amy Parish 等人强调,倭黑猩猩是以雌性为中心的:“倭黑猩猩是雌性主导的,它们通过雌雄之间以及雌雌之间的性接触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至关重要的是,雌性之间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也会形成强有力的纽带。”在倭黑猩猩群体中,雄性较少暴力,往往处于等级的底层,而高等级的年长雌性及其联盟则维持着和平。这一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即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尽管在基因上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同样接近,却拥有相反的社会结构——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父权制在我们谱系中的必然性。正如科学写作者 Angela Saini 所指出的,倭黑猩猩表明,自然界中确实存在一种母系模式,这为人类祖先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的早期古人类社会是否可能不像黑猩猩那样以雄性为主导?合作性的女性网络是否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人类并非倭黑猩猩,但这一洞见打开了对多样性的认识空间。它也为强调女性联盟与性在人体进化中作用的假说(如下文将讨论的 Chris Knight 的理论)提供了可信度,并为理解灵长类群体中女性领导如何运作提供了一种自然类比。
进化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同样开始为女性在远古过去的角色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由 Kristen Hawkes 等人提出的“祖母假说”(grandmother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人类的长寿(尤其是女性绝经及其长时间的绝经后寿命)之所以进化出来,是因为祖母对孙辈的生存做出了关键贡献。根据这一假说,在早期智人群体中,已不能生育的年长女性会帮助供养和照料孙辈,使得她们的女儿可以更快生下下一个孩子。这种祖母式照料实践会提高整个群体的繁殖成功率。这意味着,支持性强、经验丰富的女性的存在,是人类生命史进化的驱动力之一——从本质上说,人类“多代同堂”和合作育儿的状态,得益于史前祖母们。近期研究确实发现了与祖母相邻而居的进化优势(例如儿童死亡率降低)。这些发现改变了叙事:进化英雄不再只是“男人—猎人”,而是“女人—协同照料者”(共同母亲或祖母),她们作为无名英雄,确保了我们物种的成功。
“合作繁殖”这一主题——即人类是“照料型猿类”,依赖众多帮手来抚养每一个孩子——由人类学家 Sarah Blaffer Hrdy 大力倡导。Hrdy 认为,早期人类母亲不可能单独断奶并抚养拥有巨大脑容量和漫长童年的后代;她们需要亲属(包括祖母和年长儿童)的协助。这在我们的祖先中培育了前所未有的共情、沟通与社会智力。有趣的是,这一思路又回到了文化起源的问题:如果人类婴儿天生就极度依赖他人且高度社会化,而母亲又需要招募帮手,那么社会合作乃至语言的基础,很可能就根植于母婴(以及母亲—亲属)互动之中。事实上,近期学者 Sverker Johansson 在 Hrdy 的工作基础上提出,语言的进化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功于女性的合作。他指出,那些聚焦于雄性求偶竞争的理论与证据并不吻合:“一种常见假说认为,语言是通过性选择进化出来的——男人为争夺女人的注意而竞争——这一假说可以被否定。女人和男人说话的能力同样好。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的解释必须是性别中立的,或至少接近性别中立。”相反,Johansson 认为,语言是为了促进在育儿及其他社会任务中的群体合作而产生的。他提出所谓“黑猩猩测试”(chimp test):任何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都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灵长类(如狒狒或黑猩猩)同样群居,却没有进化出语言。他的答案是,早期人类处于一种独特情境之中——可能与艰难的分娩和对接生帮助的需求有关。他指出,由于直立行走和大脑体积增大,人类婴儿在出生时往往需要他人协助,而新生儿极其无助。因此,在他的情境中,接生婆和祖母成为关键角色。在 Johansson 看来,语言可能最初在女性之间(母亲和其他照料者)发展起来,作为一种相互帮助的沟通系统(“现在用力!”“拿水来!”或安抚婴儿)。在许多世代中,这些母性发声会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并被整个群体共享。这与人类学家 Dean Falk 先前提出的“母语假说”(mother tongue hypothesis)高度契合,后者认为,最初的词语源自母婴之间的“婴儿语”互动。根据 Falk 的观点,当早期古人类母亲不得不将婴儿放下去采集食物时,她们会通过旋律化的发声(摇篮曲或安抚性言语的前身)来安抚和安慰婴儿。这些富于情感的声音——本质上是一种古老形式的“母语式语调”(motherese)——逐渐获得意义与结构,为真正的语言奠定基础。随着时间推移,起初在母亲与孩子之间使用的沟通方式扩展到更广泛的家庭和群体,最终成为所有人共享的成熟语言。
这些假说强调,女性的社会与养育活动可能是人类符号文化进化的驱动因素。它们扎根于现实的进化生物学,而非浪漫化的神话,但仍然提升了女性在“何以为人”的故事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是创新与技术:从考古学上看,一些最早的文化发明很可能出自女性之手。例如,容器的发明(编织篮子、陶器)通常被归因于采集—手工艺者,在许多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情境中,这些人很可能是女性。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由女性采集者率先尝试播种而开启的。动物驯化也可能部分归功于女性,她们可能负责照料小型猎物,或照看被带回的孤儿动物。尽管直接证据稀少,但这与 Schmidt 的观察相吻合:即“女性参与了最早的植物栽培”,这提升了她们的社会重要性,并可能在早期农业社区中催生对女神的崇拜。甚至火的控制与烹饪的发明——人类文化中的关键里程碑——也可以部分归功于女性的努力:灵长类学家 Richard Wrangham 的“烹饪假说”认为,对火的掌控及烹饪食物对人类进化至关重要,而在许多采猎社会中,女性是炉火的主要守护者,也是植物食物知识的主要掌握者。虽然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哪一性别首先煮沸了水或烤熟了山药,但合理的推测是,在史前饮食文化中,女性“营养学家”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男性猎人。
有一种现代理论明确将女性置于文化诞生的中心,即 Chris Knight 颇具挑衅性的研究成果。在《Blood Relations: Menstru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e》(《血缘关系:月经与文化的起源》,1991)一书中,Knight 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与神话学,主张最初的人类符号文化是由女性的团结创造出来的。基于“性罢工”的构想,Knight 提出,早期人类雌性可能同步了排卵与月经周期(或许以月相为时间参照),并在特定时期集体拒绝向雄性提供性接触,以迫使雄性在狩猎和分享肉食方面进行合作。根据 Knight 的假说,这催生了最初的仪式与禁忌——例如月经禁忌、以红色颜料涂抹身体以象征血液,以及将时间仪式化地划分为“女性”(禁忌)与“男性”(开放)阶段。他设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 4 万年前),这种由女性主导的“罢工—庆典”动态,推动了许多考古学家所说的“符号革命”(艺术品的突然激增、个人装饰物、复杂的葬礼仪式等)。在 Knight 的情境中,女性的集体行动锻造了社会契约:猎人带回肉食,并在月经后宴会中进行分配,从而在女性主导的条件下巩固了两性之间的新型联盟。正如一则概括所说,Knight 认为,“女性通过性与月经节律,滋养了文明的原初创造冲动,并在本质上创造了人类文化。”Knight 所调动的证据范围广泛,从创世神话的共通性(例如他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 Wawilak 姐妹神话解读为月经同步与仪式起源的寓言),到采猎者与灵长类的行为模式。尽管许多人类学家认为 Knight 的理论带有相当的推测性,但它是一个严肃的尝试,试图回答一个生物性猿类如何成为文化性人类的问题——而且它通过将一群合作的女性置于这一转折点的中心,来解释她们如何发明了使社会成为可能的规则与符号。
另一方面,对现存社会的民族志与社会学研究有时也揭示出强大的女性角色,这些角色或许反映了某些祖先模式。人类学家 Peggy Reeves Sanday 在其跨文化调查《Female Power and Male Dominance》(《女性权力与男性支配》,1981)中,识别出若干社会(从西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到某些美洲原住民群体),在这些社会中,女性在财产、继承与仪式方面享有实质性控制权,尽管她们并未在形式上统治男性。Sanday 谨慎地使用“母系制”一词来描述这些案例,将其界定为一种女性利益在社会事务中占上风的情境,而非父权制的镜像。她的结论是,尽管没有已知社会是严格意义上的母系制,但女性地位存在一个光谱,一些文化确实可以被称为“以女性为中心”(gynocentric)。当代的例子如中国的摩梭人(拥有母系家庭与“走婚”制度)或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关于女性圣者的神话,都表明女性中心的社会组织并非纯属幻想——尽管在每一种情形中,男性仍然掌握某些政治或身体上的权力,从而阻止了父权制的真正颠倒。
关键在于,当代科学共识并不支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过去母系文明的存在。科学共识所支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始终是人类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采集者与创新者,作为文化与语言的承载者,作为关键社会变革中的平等伙伴(甚至在某些情境中是领导者)。正如《大英百科全书》简明指出的那样,“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人类学证据表明存在一个社会,在其中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统治男性作为一个群体。”但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社会中存在母系亲属制度,以及女性在宗教或经济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进化理论也日益承认女性能动性(通过择偶、育儿与合作)是人类进化的驱动力。简言之,“文化之母”假说的强形式仍未得到证实,但其弱形式——即母亲与祖母、智妇与女神始终是构成我们“人之为人”的基础——则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结论#
关于女性是人类处境的开创者与文化的奠基者这一观念,其历程复杂多变,从神话到推测再到科学分析。它最初诞生于神圣故事的领域:关于女神与第一位女性的传说,她们创造世界、颁布律法、传授技艺。19 世纪,Bachofen 等学者将这些故事转化为宏大的历史理论,设想曾经存在一个女性影响力至高无上的时代,人类文化由“母权”而生。这一大胆论题吸引了许多人——Morgan、Engels 等——他们将其与新兴知识相结合,主张早期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直到私有财产或新神祇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随着时间推移,证据与意识形态风向都发生了变化。人类学家收集到的数据推翻了简单的普遍母系制设想,但这一概念的魅力依旧存在,并被每个时代的关切重新塑造: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捍卫者予以否定;极权政权对其加以挪用或扭曲;女权运动将其重塑为赋权神话;而人类学家则通过灵长类行为、化石与亲属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它。
从这段历史中浮现出来的,是一种更为丰富的对女性在人类进化中角色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需要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母系王国。女性作为创造者——当然是生命的创造者,但同时也是生计策略、安慰性语言、分享网络与神圣意义的创造者——始终处于我们物种的中心。随着理解的加深,我们发现问题不在于女性是否是文化某些方面的开创者,而在于她们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方式上发挥这一作用。现代研究表明,诸如延长的童年期(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合作繁殖与沟通等发展,可能在同等程度上依赖于 X 染色体与 Y 染色体。神话中的“第一位女性”或许并未独自统治,但她以及她在早期古人类中的现实对应者,确实帮助塑造了人类故事——不是通过一个毫无痕迹地消失的黄金母系时代,而是通过那种持久而不可或缺的工作:抚育每一代新生命,维系使文化成为可能的纽带。
常见问题解答(FAQ)#
Q 1. 什么是“原初母系制”假说?
A. 这是一个由 J.J. Bachofen 在 1861 年及后来的思想家所普及的理论,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性在社会、政治或精神层面上拥有主导权(“母权”),这一阶段通常与母系继嗣和女神崇拜相联系,随后才被父权制所取代。
Q 2. 是否存在关于古代母系社会的科学证据?
A. 没有。尽管许多神话中出现强大的女性形象,一些社会也确实是母系继嗣或母性中心的,但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的学术共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曾经存在一个时代,在其中女性系统性地作为一个群体统治男性作为一个群体。这个概念如今更多被视为一种历史理论或神话本身。
Q 3. 如果母系制并不真实存在,那么学者们今天如何看待女性在文化起源中的角色?
A. 研究如今聚焦于具体、基于证据的贡献:例如“祖母假说”(女性长寿有助于后代存活)、女性在发明农业或早期技术(陶器、编织)中的可能角色、母婴沟通在语言起源中的重要性(“母语式语调”假说),以及灵长类学所提示的女性社会策略(如倭黑猩猩研究)。女性被视为进化与文化中的核心行动者,但不必被设想为一个失落母系世界的统治者。
参考文献#
- Wawilak Sisters (Dreamtime) – Yolngu creation myth
- Changing Woman – Navajo origin myth
- Amaterasu – Japanese sun goddess & imperial ancestress
经典“母系制之争”#
- Johann Jakob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1861)
- Encyclopedia overview of Bachofen & later reception
- Lewis Henry Morgan, Ancient Society (1877)
-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 Sir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1861)
- John F. McLennan,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1886)
- Edvard Westermarc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1891)
- Jane Ellen Harrison,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1903)
- Jane Ellen Harrison, Themis (1912)
- Robert Briffault, The Mothers (1931)
- Bronisław Malinowski,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
- Wilhelm Schmidt,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World Cultures (1930)
- A. R. Radcliffe-Brown, “The Mother’s Brother in South Africa” (1924)
- E. E. Evans-Pritchard, “Some Remark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Kingship” (1930)
- Alfred Baeumler & Alfred Rosenberg – Nazi-era Bachofen reception (overview)
- Cynthia Eller, The Myth of Matriarchal Prehistory (2000)
- Marija Gimbutas, 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 (1974)
- Elizabeth Gould Davis, The First Sex (1971)
- Merlin Stone, When God Was a Woman (1976)
- Peggy Reeves Sanday, Female Power and Male Dominance (1981)
-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949) – critique of matriarchy myths
- Joan Bamberger, “The Myth of Matriarchy: 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 (1974)
灵长类学、育儿与语言进化视角#
- Amy Parish, “Female Relationships in Bonobos (Pan paniscus)” (1996)
- Kristen Hawkes et al., “Grandmothering, Menopause,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ife Histories” (1997) PNAS
- Sarah Blaffer Hrdy, Mothers and Others (2009)
- Sverker Johansson, The Dawn of Language (2021)
- Dean Falk, “Prelinguistic Evolution in Early Hominins: Whence Motherese?” (2004)
- Chris Knight, Blood Relations: Menstru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e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