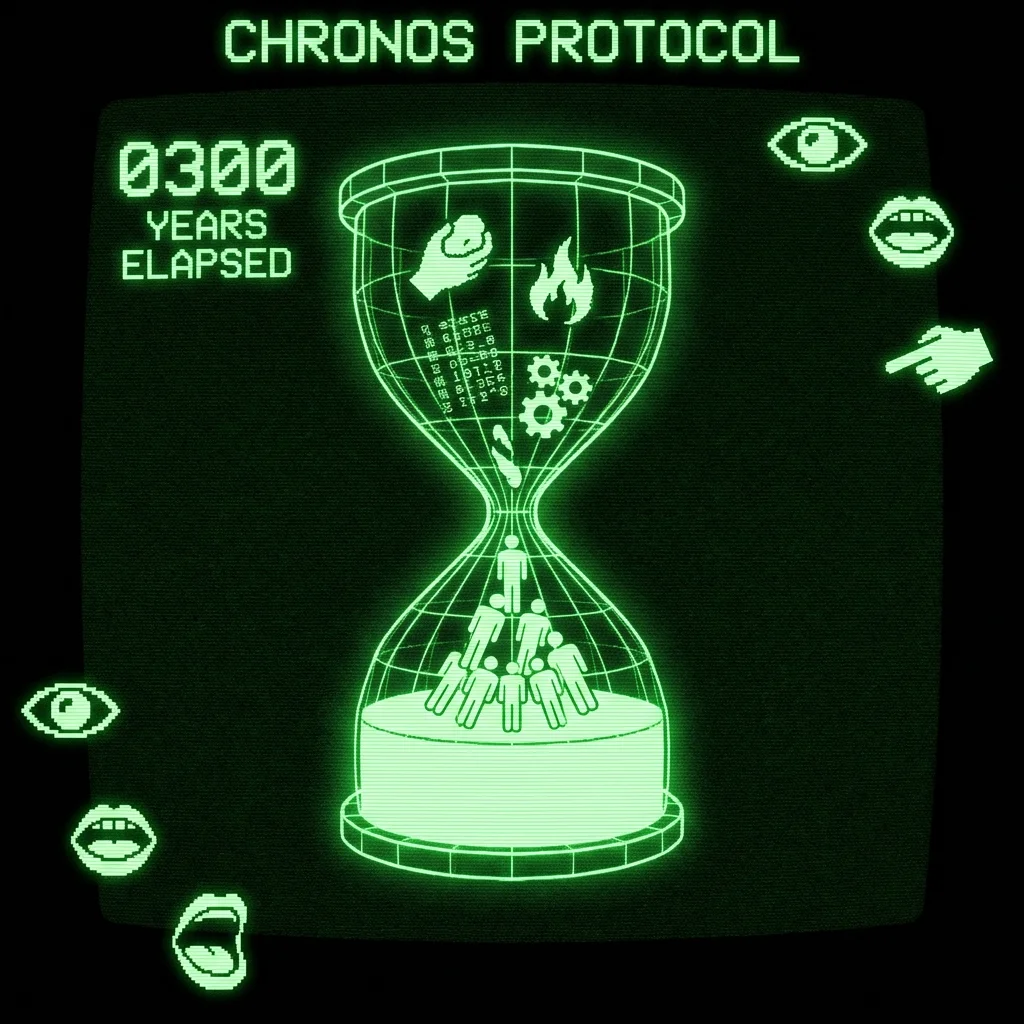TL;DR
- 达尔文认为,在语言出现之后,人类进化主要被社会力量所塑造。
- 达尔文相信重大的进化变化(道德、社会方面)发生得很快,在历史时间尺度内(以世纪计,而非以地质长时段计)。
- 他将人类视为刚刚从“野蛮”状态中走出,传统与神话中保留着过去选择压力的回声。
语言、名誉与早期人类的适应度#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一旦早期人类变得具有社会性,尤其是在发展出语言之后,名誉管理(即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关切)便成为自然选择中的关键因素。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将“同胞的赞扬与责难”视为塑造道德行为的强大刺激。他主张,人类的社会本能(如同情心)使他们喜爱赞扬、畏惧责难,从而改变其行为。即便是“最粗野的野蛮人也感到荣耀之情,这从他们保存自己英勇战利品……以及极度夸耀的习惯中可见一斑”——如果他们不在乎他人意见,这些行为“就毫无意义”。换言之,一旦交流与群体生活使个体能够彼此评价,那些追求尊敬(或避免羞耻)的人,在部落内部便获得了选择优势。
达尔文推断,这种倾向在人类进化的极早期就已出现。虽然“我们当然无法说出”我们的祖先究竟在多早的时候就能被赞扬或责难所驱动,但他指出,连狗都能理解他人的鼓励与责备。因此,一种初级的社会认可感很可能早于完整语言而出现,但随着语言的发展,这些社会压力被大大强化。达尔文得出结论:“原始人类在极其久远的时期,就已受同伴的赞扬与责难所影响”,这意味着对名誉的关切——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道德感——早已存在于人类遥远的祖先中。在他看来,对他人认可的关注成为适应度的关键驱动力:遵守群体规范(赢得赞扬)的成员会被信任和支持,而招致责难者则可能被排斥或惩罚。达尔文强调,“在粗野时代,热爱赞扬与畏惧责难的重要性几乎难以被夸大”,因为即使一个人缺乏深厚的天生利他主义,他也可能“出于荣耀感”而英勇自我牺牲,从而造福其部落。此类由名誉驱动的行为会激励他人,并可能比单纯繁衍后代的基因贡献更为重要。总之,达尔文认为,语言与社会交流的出现,使社会本能成为一种强大的进化力量:道德行为以及对荣誉或羞耻的管理,成为人类群体中生存与繁殖的核心。
文化作为选择力量:语言、良心与制度#
达尔文在著作中反复将文化——包括语言、智力、道德与社会制度——视为引导人类发展的关键进化力量。他认为,自然选择最初赋予人类同情等社会本能,但一旦社会形成,文化因素便开始塑造人类进化的方向。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描述了简单的社会本能如何在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逐渐演化为复杂的人类良心:“最终,我们的道德感或良心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情感——起源于社会本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同胞赞许所引导,由理性、自利心以及后来的深刻宗教情感所支配,并由教化与习惯加以巩固。”在此,达尔文勾勒出一种基因—文化互动:先天本能提供基础,而良心则通过对后果的理性思考、宗教或哲学教义,以及社会中传承的教育与习惯而被精细化。
重要的是,达尔文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社会学习与制度成为“适应度”的主导驱动力,即便生物进化仍在更隐微地持续。他观察到,在“高度文明的民族”中,直接的自然选择不如在野蛮人中那样强烈(因为现代社会不会在战争中不断互相灭绝)。取而代之的是,差异性的成功通过文化途径实现。依达尔文之见,对于文明人而言,“更有效的进步原因”是“青年时期良好的教育……以及由最有才能与最优秀的人所灌输的高尚卓越标准,这些标准体现在国家的法律、习俗与传统中,并由公众舆论加以执行。”简言之,教育与社会规范(本身是语言与集体知识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个人与群体能够兴盛。公众舆论——本质上是群体的赞许或不赞许——强制执行那些通向成功的行为。然而,达尔文谨慎地指出,即便这种由公众舆论进行的约束也可追溯到生物学:“公众舆论的执行取决于我们对他人赞许与不赞许的欣赏;而这种欣赏则奠基于我们的同情心,而同情心……最初是通过自然选择发展出来的,是社会本能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道德、法律、制度等文化进化,是建立在生物进化出的倾向(同情与社会认可)之上的。
达尔文还将语言本身视为进化的产物与驱动力。他引用当时语言学家的研究,指出“每一种语言都带有其缓慢而渐进演化的痕迹”,与生物进化类似。语言使更好的协调、知识传递以及诸如义务或正义等抽象观念的形成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选择。例如,共享的语言使一个部落能够发展出集体良心与传统体系,从而提升其凝聚力与成功率。在达尔文看来,一旦人类发展出哪怕是原始的语言与推理能力,文化选择便开始引导我们的智力与道德能力。在一段颇为著名的论述中,他推测,如果某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新工具或武器,“最朴素的自利心”会驱使他人加以模仿;那些采纳有用创新的部落会扩张并取代其他部落。这就是文化进步对生存的影响。更进一步,拥有更好治理与社会凝聚力的部落(达尔文称之为“服从”与组织的优势)会胜过混乱无序的部落。在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对制度(政府形式、服从与合作规范)具有进化后果的洞见。总而言之,达尔文将人类进化框定为一个双层过程:自然选择赋予我们语言、社会情感与智力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又使文化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选择环境——得以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地由观念、道德与社会结构所支配,而这些因素可以迅速变化,从而在远短于典型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上推动进化结果。
文明与野蛮:从野蛮祖先到道德进步#
达尔文坚信,现代文明人距离“野蛮”状态并不遥远,且文明只是一层覆盖在更古老野蛮本性之上的薄薄外衣。他援引人类学证据,表明所有文明民族曾经都处于野蛮状态,并逐渐自我提升。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一些同时代人(如阿盖尔公爵或惠特利大主教)的观点,这些人认为早期人类起初处于先进、文明的状态,后来才堕落。他称他们的论证与“人类以野蛮人身份来到世界”的证据相比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所谓堕落的案例远远少于进步的案例。对达尔文而言,“人类总体上进步多于退步”是一个“更真实也更令人振奋的观点”,人类“虽然以缓慢且时断时续的步伐,却已从低微状态上升到迄今为止在知识、道德与宗教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标准。”这种进化人文主义——即认为道德与智识会随时间进步——贯穿了达尔文对历史的解读。
关键在于,达尔文认为许多道德或心理变化发生在相对近期(以数百年或数千年计,而非以地质长时段计)。他指出,一些我们如今视为根本的美德曾经并不存在。例如,节制、贞洁与远见等特质在早期时代“完全不被理会”,但随着文明发展,后来却被“高度推崇,甚至视为神圣”。这意味着,当人类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大型文明时,道德发生了快速的文化进化。达尔文举例说,没有任何古代民族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文明世界中近来的发展。同样,正义这一概念本身也经历了转变:“原始的正义观念,如战斗法则与其他习俗所显示的那样……极其粗陋”,也就是说,早期社会往往通过战斗或复仇来解决争端,而不是依据抽象原则。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粗糙做法被更精细的伦理与法律规范所取代。用达尔文的话说,“最高形式的宗教——即上帝憎恶罪恶、热爱正义的宏大观念——在原始时代是未知的。”早期宗教与迷信纠缠在一起,并不必然促进道德善,而后来的宗教思想(在“更高等”的信仰中)则融入了强烈的伦理成分。所有这些变化——婚姻习俗、正义观与宗教——都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之内。
通过考察“野蛮”社会与历史记录,达尔文认为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看到早期的自己。他指出,“许多现存迷信是过去错误宗教信仰的残余”,甚至在现代社会中也被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达尔文认为,一个社会中的“道德标准与天赋良好之人的数量”可以在历史时间内通过群体竞争而上升。如果某个部落或民族拥有鼓励更多爱国、忠诚、服从、勇气与同情的文化特质,它就会“在大多数其他部落之上取得胜利;这就是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看来,历史是一系列此类斗争的持续过程——“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时代,部落不断取代其他部落;而由于道德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标准……因而会在各处趋于提升。”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张:它暗示在短短几代人或几个世纪内,一个具有更优“道德构成”的社会就可能扩张,以牺牲其他社会为代价,从而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时间尺度上提升人类的道德本性。
达尔文也承认,进步并非自动或普遍。有些群体在长时间内停滞不前。他观察到,“许多野蛮人在几个世纪前首次被发现时所处的状态,与他们现在的状态相同”,提醒我们不要将进步视为必然。环境与社会因素必须配合,进步才会发生。尽管如此,他所看到的总体轨迹仍是向上的。那些“文明民族”,凭借科学、教育与开明制度,代表了人类从野蛮攀升的近期顶点。重要的是,达尔文并不认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存在根本的生物学鸿沟——只有程度与文化的差异。文明人仍然保留着“其卑微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达尔文著名的表述所言,这意味着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本能与激情仍然透过文明的外衣隐约可见。简言之,达尔文将文明描绘为建立在更古老基础之上的一层近期文化进化,其明确含义是:在合适的压力下,我们的道德与心智能力可以在短暂的进化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
达尔文对短期进化时间尺度的看法#
达尔文最耐人寻味的立场之一,是他在涉及人类时,乐于接受在惊人短时间尺度上发生的进化变化。不同于在地质年代中缓慢运作的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眼中,人类的进化——尤其是精神、道德与社会特征——可以在短短数百年或数千年内发生。他回顾历史,看到自然选择在历史时间中发挥作用,产生了各民族之间可观察到的差异。例如,达尔文将十八、十九世纪美国的迅速崛起归因于仅仅几百年内起作用的选择过程。他写道:“显然有相当多的道理可以相信,美国的惊人进步以及其人民的性格,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过去十到十二代人中,来自欧洲各地更有活力、更不安分、更勇敢的人纷纷移民到那个伟大的国家,并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这里,达尔文明确将一种进化效应压缩在“十到十二代人”(大约250–300年)之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他认为,通过性格的筛选与差异性成功,已经塑造了整个国家的性格——这是一个由文化迁移与竞争驱动的快速进化变化的清晰例证。
达尔文还思考了人群之间命运如何迅速逆转。他指出,在几个世纪前,欧洲曾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而在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晚期,欧洲列强已远远超越奥斯曼帝国。在1881年一封私人信件中,达尔文将此视为自然选择在文明中运作的证据:“记住,在不算太多世纪之前,欧洲各国曾面临被土耳其人淹没的风险,而如今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更文明的所谓高加索人种在生存斗争中彻底击败了土耳其人。”随后他将这一趋势外推至未来,预测“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以世纪来衡量的时间内,无数低等人种将被更高等的文明人种所消灭。”事实上,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已发表过类似(而今声名狼藉)的预言:“在未来某个时期,以世纪来衡量并不算太遥远,文明人种几乎肯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并取代野蛮人种。”达尔文所设想的时间尺度——“以世纪来衡量并不算太遥远”——凸显了他相信几百年足以在人类中产生显著的进化更替。这些言论虽令现代读者感到不安,却展示了达尔文的逻辑:技术与社会优势(文化的产物)会迅速转化为在全球范围内的生存与繁殖优势。他认为文明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会在进化意义上迅速取代较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如自然界中更适应的变种取代较弱者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并未将这些过程视为完全良性。他也意识到,文明同样改变或放松了某些自然选择压力。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观察到,在文明社会中,弱者与病者往往被保护而非被淘汰,“我们竭尽所能阻止淘汰过程;我们为弱智者、残疾者与病人建造收容所……并通过接种疫苗来保全生命”等。他承认,“除了人类自身之外,几乎没有谁愚蠢到会让自己最差的动物繁殖。”这意味着自然选择的作用被阻碍,可能允许某些特质的“退化”。然而,达尔文并不主张放弃同情;相反,他认为帮助弱者的冲动是我们社会本能的延伸,而“承受弱者存活并繁衍其类所带来的无疑不良后果”,只是我们为自身最崇高部分——同情心——所付出的代价。其结果是,即便在自然选择减缓的情形下,文化力量(如伦理与同情)也介入其中,并自身成为进化因素。
总体而言,达尔文关于时间尺度的假设是大胆的:他愿意将人群之间的差异解释为仅仅几十代选择的产物。无论是在讨论更有活力的美国人的形成、一个帝国的衰落,还是部落社会可能的灭绝时,达尔文都一贯强调,当进化由激烈竞争或新环境驱动时,其作用可以多么迅速。在他看来,人类进化并未在遥远的过去停止——它仍在持续,并且被迁徙、战争、社会结构等人类历史的核心变化所加速。
传统与神话:野蛮选择压力的残迹#
达尔文认为,文化传统与古老神话往往保留着我们野蛮过去的回声,包括早期人类所面临的残酷选择压力。在他搜集文明民族源自野蛮人的证据时,他指出,在“仍然存在的习俗、信仰、语言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曾经低微状态的痕迹。”许多以仪式或故事形式延续下来的习俗,在达尔文看来,曾经是早期时代的真实实践。例如,达尔文(借鉴人类学家J. F. McLennan等人的研究)指出,“几乎所有文明民族仍保留着诸如强行掳妻等粗野习惯的痕迹。”在现代婚礼仪式或民间传说中,可能存在抢婚的残余表演;这暗示在遥远的过去,掳妻与部落劫掠是真实而普遍的行为,塑造了社会行为的进化(如男性联盟、攻击性或女性择偶)。同样,达尔文反问道:“有哪一个古代民族可以被称为最初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这表明,那些关于嫉妒的神祇与后宫的普遍故事,或神话英雄的多妻安排,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多妻状态。许多文化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会施加新的选择压力(例如更大的父亲投入,或性竞争以不同形式展开),而古老神话则是通往先前现实的一扇窗口。
也许达尔文给出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出现在宗教与道德领域:人祭这一在达尔文时代几乎被彻底消除的实践,却在文明民族的故事与经典中存留。达尔文引用Schaaffhausen教授的观察,指出“在荷马与《旧约》中都发现了人祭的残迹”。的确,古希腊史诗与《圣经》中包含一些暗示(如阿伽门农献祭伊菲革涅亚,或亚伯拉罕几乎献祭以撒),表明在更早的时代,人们确实以人命祭神。达尔文将这些残余视为重要证据:它们表明,即便是我们“文明”谱系中的直接祖先,也经历过一个野蛮阶段,在那时此类残酷实践是适应性或规范性的。例如,仪式性人祭可能起到团结部落或威慑敌人的作用——从而对某些心理特质(如狂热、服从或群体从众)施加选择压力,这些特质一直持续,直到新的社会规范演化出来。神话中关于献祭儿童的回声(如亚伯拉罕的故事,最终禁止此举却清楚地记得它)在达尔文看来,表明“几乎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显示其曾经历过一个野蛮时期”,在那时极端行为十分常见。即便是迷信与民间信仰,他写道,“也是过去错误宗教信仰的残余”,作为文化化石被保留下来。许多禁忌习俗(例如神话或传说中的仪式性食人或杀婴)在达尔文看来,很可能曾是现实行为,在严酷环境中带来某种生存优势——也许是控制人口规模,或恐吓对手——只是后来才被逐步废除,并以恐惧的方式被记忆。
达尔文自己的性选择理论也在文化残迹中找到支持。关于英雄掳妻的神话,或女性选择勇士与歌者的传说,反映了他所认为的史前现实,这些行为影响了人类本能甚至身体差异的进化。他还以计数艺术为例,说明文化实践如何保留其原始起源:我们仍用“score”表示20,或在数字系统中保留用手指计数的痕迹,这表明早期人类确实用手指与脚趾来计数。这个看似无害的例子强调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原始语境消失后长久存留,作为过去选择压力的线索。在达尔文的综合视野中,人性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解释或“凭空而来”的——它要么具有当前用途,要么有其历史原因。因此,传统与神话是理解人类进化的数据宝库。它们讲述了一个时代,在那时如今被视为不道德或怪异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存挑战的适应性回应。
总之,达尔文将人类习俗视为一幅重写羊皮纸(palimpsest):在我们的仪式、故事与语言表层之下,潜藏着“曾经低微状态”的褪色却可辨认的记录。抢婚、血仇、决斗审判或人祭等实践在文化记忆中留下了痕迹,达尔文利用这些痕迹来强化他的论点:我们的祖先曾在野蛮状态中生活了漫长岁月。这个虽残酷却真实的深层过去,为随后的快速道德进化奠定了舞台。通过识别这些残迹,达尔文展示了基因与文化如何跨时间互动——旧的文化实践通过选择某些特质来塑造生物学,而后来的生物倾向(如我们的社会本能)又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
FAQ #
Q 1. 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已经停止了吗?
A. 否。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仍在持续,并且被迁徙、群体间竞争以及社会制度发展等文化因素所加速,这些过程在以世纪计的短时间尺度上发挥作用。
Q 2. 达尔文如何看待进化中生物学与文化的关系?
A. 达尔文认为存在基因—文化互动。生物学(如同情等社会本能)提供基础,而文化(语言、理性、规范、制度)在文明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塑造人类发展与适应度。
Q 3. 在达尔文看来,名誉在早期人类进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A. 达尔文认为“热爱赞扬与畏惧责难”至关重要。一旦语言使社会评价成为可能,管理自身名誉便成为部落内部生存与繁殖成功的核心。
Sources#
- Darwin, Charles.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2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74. (First published 1871). — Especially Chapters IV and V, which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sense, the social instincts, and the evidence of humanity’s primitive origins. Darwin’s own words are quoted extensively above, with page references to the 1874 edition (e.g. pp. 131–145).
- Darwin, Charles. Letter to William Graham, July 3, 1881,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ed. Francis Darwin,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87, pp. 315–317. — In thi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Darwin reflects on The Creed of Science and argues that natural selection has actively shaped human progress in recent history, citing the triump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over others. This letter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of Darwin’s belief in short-term evolutionary change driven by cultural factors.
- Darwin, Charles. Letter to John Morley, April 14, 1871, in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eds. Francis Darwin and A. C. Seward,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pp. 241–243. — Darwin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regulation of the moral sense, responding to Morley’s review in the Pall Mall Gazette. He clarifies his views on conscience as founded in social instincts and influenced by utilitarian standards, which aligns with the role of sympathy and public opinion in moral evolution. (This source sheds light on Darwin’s thinking behind the published text in Descent of Man.)
- 达尔文,查尔斯。《人类的由来》,第1版。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1871年。—(通过上文所引的第二版被隐含引用。)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第225页)包含达尔文关于文明种族取代野蛮种族的预言。第一版是那段关于未来消灭“野蛮种族”的常被引用语句的主要出处,展示了达尔文以出版形式提出的短时间尺度预测。(第二版保留了这一段落,仅作了轻微修改。)